

(攝影/陳昭旨)
台妹是一種很玄的東西。台妹的打扮千變萬化,台妹的心情捉摸不定,台妹是少女,是輕熟女,也是人妻。那些遠去而美好的時光裡,有台妹、有台客、有台T,混亂的歲月糾纏如繭,經過洗練,蝴蝶才能破蛹而出。「台妹」這名字,也來自別人對陳雪的標籤,這標籤曾經使她困惑,卻也帶來溫暖。總括青春與童年,收攏麵攤小吃攤上的熱騰騰煙霧,往事其實並不如煙,只是被層層包圍,那是夜市人生,那是橋上的孩子,也是陳雪的《台妹時光》。
回頭書寫舊時光跟食物,對陳雪來說,就像檢閱人生的照片,「那是我20來歲時候的事情,像是放暑假的人,去外婆家住一個夏天,跟這些人發生一些事。對我們來說都是很重大、很難忘的事,但年輕時並不知道。」
陳雪不重視飲食,但她年輕時的交往對象都很懂得吃,他們不去咖啡店、不談小說和電影,卻會特地驅車到某地覓食,而她就像浮萍,待在摩托車後座或汽車副駕,隨著他或她四處遊蕩。直到跟早餐人結婚後,陳雪從紀錄食物的製作過程中,漸漸產生改變,進而能夠捕捉過往,寫下那個台味,寫下置身其中的自己。記憶歷歷在目,如同翻閱舊相簿,她找到召喚的法術,記下那些人、那些事、那個夢一樣的夏天。
陳雪以片段開始回溯,她的故事時間軸愈拉愈遠,從20來歲的戀愛寫至童年。「我是一點一點地深入自己的台。」她笑著解釋,「我沒有想要評價什麼,只想用經過這麼多年鍛煉過的文筆,把人的故事還原成時間的切塊,試著把它描繪出來。」作為一個台北人、都市人,即使到現在,陳雪還是無法以都市人的身分愜意生活,總是擔心哪裡出了錯,好像總有什麼跟都市格格不入。「有些優雅精緻的東西讓我感覺壓抑。來台北之後,反而對過去的那些時光,感覺更加愛惜。」即使回不去了,在記憶深處,舊時光仍舊傳遞來溫暖。
確立小說家身分之前,陳雪是手錶業務員。「我以前非常痛恨我做的那個工作,因為它把我一天14個小時都綁住了,送貨、調整手錶、擦壓克力櫃,整天都在路途上。」新來的錶時間都是錯的,時間很容易跑掉,「業務員陳雪」總是在對時、總是在校正時間,「校正時間變成我人生的一個隱喻,『陳雪』的時間已經流失了,每天都在對手錶,根本沒時間寫小說。」有幾次,她在書局跟人結算手錶帳款,一旁就陳列著她的書,她無法以「小說家陳雪」的身分簽收帳單,也不好意思告訴別人她在寫作,只能努力地把這個身分保護起來。
那時,陳雪家裡投資手錶生意,送錶工作維繫了全家生計,寫作反倒像是在破壞家庭幸福。「一想到寫小說,就沒辦法把工作做好,可是我滿腦子都想寫小說啊。所以我常常送貨到半夜,犧牲睡眠時間寫到早上。」身分上的衝突困擾陳雪許久,送貨的台妹人生跟寫作的小說生涯互相拉扯,直到近幾年,她才有辦法用自然的語言跟人聊天,進而談論自己的作品。往事帶來創傷,有陣子她很討厭手錶、討厭夜市,連聽到類似的喧嘩聲都感到頭痛,本能地產生排斥。「現在都不會了,都不會了才可以很平靜的去寫。我出《橋上的孩子》的時候還是有些埋怨,有解脫不了的痛苦。那段時間對我還蠻珍貴的,有兩三本小說就是在送貨的期間寫的,以前的我不珍惜這些經驗,覺得是阻礙,現在會感念,帶著豐富的感情回味那些歲月。」
陳雪形容這過程,像是小動物在學習如何做一個人。「我認識的很多人都是跟他的周遭環境格格不入的,那個格格不入、不合時宜、摸索語言,我不覺得那是社會化,而是人在形塑一個獨一無二的自己。」過程即使痛苦,卻非常珍貴,那些時光是一生順利的人得不到的。「我以前覺得自己總是在講錯話,這件事困擾我蠻久的。寫作可以讓我有安身之處,在現實世界尋找一種表達自己的方式。」像是遲疑了多年未能說出口的告白,陳雪說,「現在我可以面對了,其實我是個台妹。」
〔散文.快問快答〕
Q1. 您自己在散文寫作時,對真實與虛構的態度是?
陳雪:我不認為虛構就是假造,在小說裡,虛構是一個非常複雜的東西。寫這些散文,我情真意切,可是你要說這樣的寫法不是虛構嗎?我沒辦法肯定地說。它不是照相、不是紀錄片,我是從記憶裡叫喚出那麼遙遠的時光,我寫小吃攤左邊是蒸籠,我能確定嗎?我不能確定,只是試圖去捕捉、去接近。
散文可不可以虛構,重要的是你想要表達的東西。如果你需要透過虛構去表達,那你是否真切地把你想表達的表達了?我覺得散文需要真切的心。我是小說家,散文對我來說不是必要寫的東西,我特別來寫了散文,是因為我有很真切想表達的東西。
Q2. 您最喜歡的散文作家是?
陳雪:李維史陀跟木心。我在寫《附魔者》的時候,很仔細地讀過《憂鬱的熱帶》,他用我理解的散文方式在陳述事實。木心是年輕的時候就讀的,他能寫詩又能寫小說,散文也非常好看。我比較喜歡可以敘述事情的散文。
Q3. 看過印象最深刻、至今記憶猶新的一篇散文是?
陳雪:李維史陀《憂鬱的熱帶》裡的〈日落〉。他仔細寫了日落,那段我曾經抄寫過很多遍。賴香吟在〈生手的天真〉裡也引用過。
〔陳雪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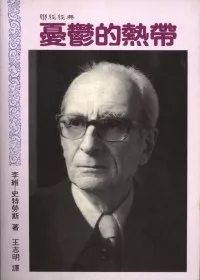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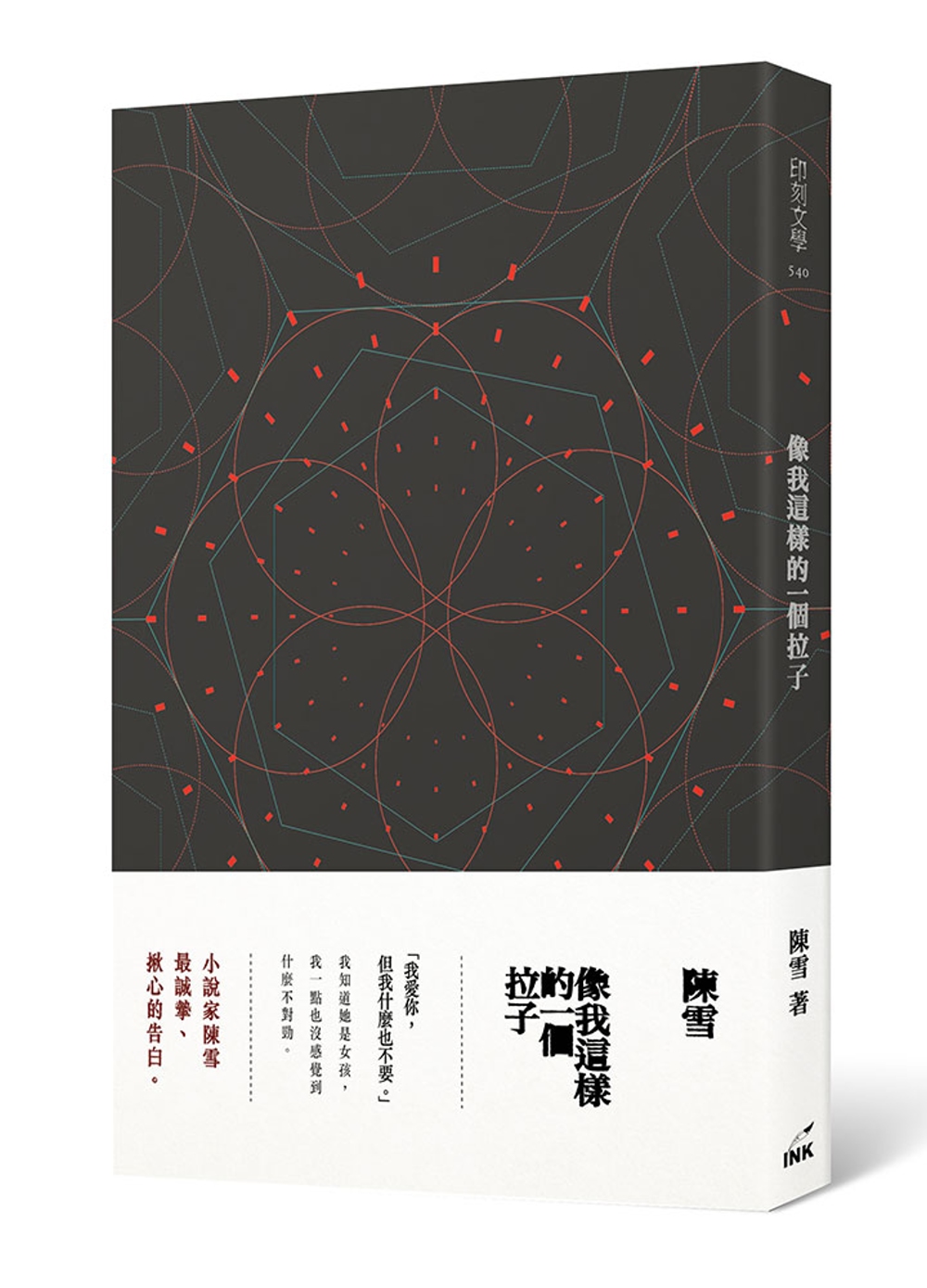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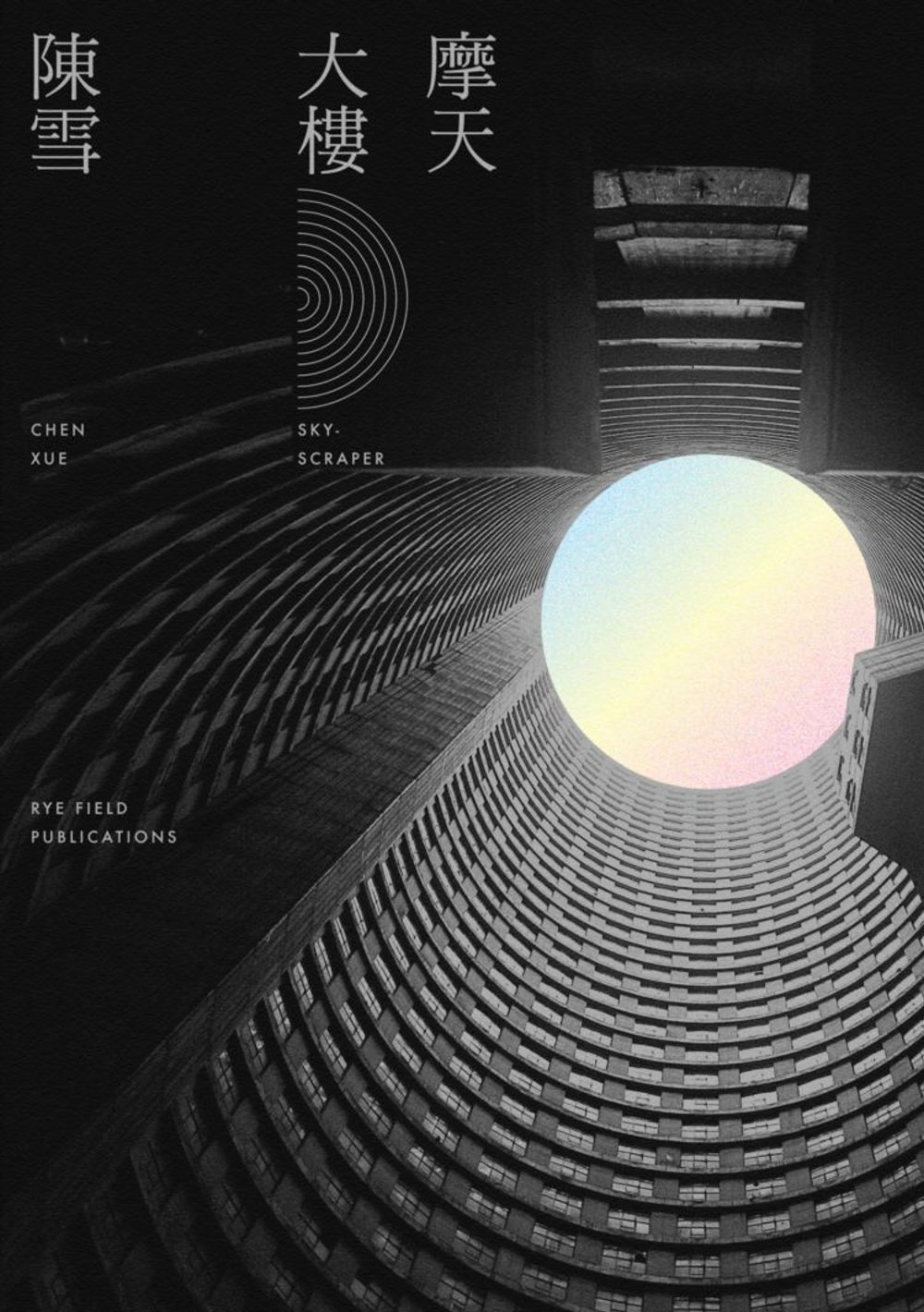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