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曾在OKAPI提過歐陽子。
談台灣同志文學史,一般都上溯到1960年代初現代主義(或謂「現代派」)小說家白先勇的短篇(這幾年來我試圖尋找比白先勇還早的台灣同志文學寫作者,但我一直找不到,還因此在OKAPI開天窗好幾次;我想開了,就把起點設在白先勇吧──就算真的挖出什麼隱士比白先勇更早,也不可能找出比白先勇作品更具歷史里程碑意義的古早佚作)。或者可以這樣說:台灣同志文學和現代主義小說,都剛好是從白先勇開始(值得注意的是,在其他國家,如英美日,同志文學和現代主義小說是各自為政的,並未同步發生)。在肯定白先勇之餘,也該留意其他同期作家的貢獻:難道當年同志文學和現代派小說的先驅都是白先勇和其他男作家,而女作家都沒有功勞嗎?

在歐陽子對現代主義文學的貢獻慢~慢~被學界肯定之餘,她在同志文學的創發也很可觀。不過她寫的同志在哪裡?
第一審來自白先勇。白先勇寫給《秋葉》的〈序〉中點明〈最後一節課〉(1967刊在《現代文學》)有師生同性之愛,並說文本中男老師愛上男學生該讀為「跟他失落的自我在戀愛」。這一篇小說中有同性之愛(論事不論人),但當事人是不是同性戀者(論人不論事的話)則是無法確定的。(我本人的立場是:我不覺得我們應該用「晚近的同志身分」「回溯」套用在這篇1960年代的曖昧角色上。)白先勇並沒說《秋葉》另含其他同志小說。
第二審來自受過女性主義訓練的學者。范銘如在《眾裡尋她──台晚女性小說縱論》(原2002,新版2008)指出,《秋葉》中〈素珍表姐〉(1969《現代文學》)所寫的「姐妹情誼」含有「同性情慾」的可能(見范92~93頁)。這個女女相愛的可能性,白先勇未曾提及(他可能也沒查覺)。要說這個文本展現了女同志可能太牽強(范並沒這樣說),但文本中的同性情慾若隱若現,是不能斷然否認的。除了范銘如之外,別的學者應該也在《秋葉》的其他文本中發現「姐妹情誼」的其他組合。
第三審來自張誦聖。出身台灣、在美執教多年的張誦聖,是台灣文學研究教學在美國的少數推手之一。她在代表作《現代主義和鄉土文學的挑戰》(Modernism and the Nativist Resistance, 1993) 中犀利剖析《秋葉》,並指出〈近黃昏時〉(1965原刊《現代文學》但1980修改後才結集)內有「(男)同性戀愛人」和「異性戀生活」。白先勇在〈序〉中指出這篇小說含有(被替代的)亂倫(後詳),並沒有說出文本中的同性戀。我也沒看出文中的同性戀。但張卻「看到了」,而且她的讀法也有道理。
簡而言之,〈近黃昏時〉的主要角色有三:一個熟女媽媽,這個媽媽的青年兒子,以及這個兒子的男性好朋友。媽媽愛吃年輕男孩,便跟兒子的好友上床。而兒子就跟他的朋友(媽媽的小情夫)起了爭執。白先勇說的(替代性)亂倫,就是:媽媽幾乎跟親兒子上床了,只不過是改跟兒子的好友做愛。
而張卻認定這個兒子和好友根本就是同性戀愛人,好友想要藉著跟男友的母親上床而「轉性」為異性戀「正常人」。張也沒說錯:在小說中,好友表明「我要過正常生活」──我本來以為這句話的意思是「我不該再跟好友的母親做愛」,而張應是讀為「我要跟女人做愛而不要再跟男人做愛」。這句話是有兩種詮釋的可能。好友說,「(我要)過正常生活…… 找個女孩子結婚……」──這也有兩種可能:找女孩而不再找熟女,或找女孩而不再找男孩。
但兒子對好友說的話應該就只有單種意思了:「讓我們回到過去的日子……我們天生如此乾脆認了……到我房裡來……」這兩人應(曾)是同性戀愛人了。
不能小看文壇和學界的前輩;她們經常比晚輩勁爆多了。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比較文學博士。作品曾獲聯合報文學獎中篇小說首獎與極短篇首獎等。著有短篇小說集《感官世界》、中短篇小說集《膜》,以及評論集《晚安巴比倫:網路世代的性慾、異議與政治閱讀》,編有文集《酷兒啟示錄:台灣QUEER論述讀本》、《酷兒狂歡節:台灣QUEER文學讀本》,並譯有小說《蜘蛛女之吻》、《分成兩半的子爵》、《樹上的男爵》、《不存在的騎士》、《蛛巢小徑》、《在荒島上遇見狄更斯》等多種。現為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專任助理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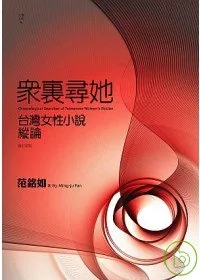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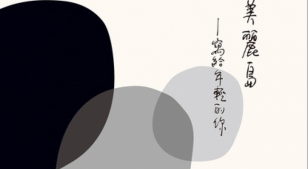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