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厚心得
戰友間的文學相伴──讀楊牧、瘂弦來往書簡
作者:楊照 內容提供:印刻 / 2024-02-02 瀏覽次數(4482)
楊牧和瘂弦的文學、思想尺度差異,累積了一、二十年,在一封寫於一九七八年二月的信中爆發出來:「...我近來也覺得『聯副』相當保守。比馬各時代更保守。我自己有些悵惘,這是實話,不怕對你說。月前讀『聯合報』上陶百川先生論時政,他特別提到吾人不應過份的『自我檢查』,我真為此老先生支偉大心懷所感動,我願請你也想想這一點。此生能做的使社會進步的事,我們都有責任去做;更怎能在這種抱負上瞠乎陶老先生之後?光風霽月,與你共勉。」
然而在台灣必須面對的現實是:「葉步榮來信說,被警總認為文字不妥事,最好不要再發生,目前台北同業競爭激烈,有些書店(出版社)在市場上競爭不過我等,就用卑下手段來中傷陷害,所謂樹大招風是也。沈燕士已親自去警總與主辦者...見過面,得悉果然是有人投書檢舉的,據說,投書中傷我們的已有數起,我們不得不小心。」
書信往來的大部分時間中,楊牧的主業是留學生、學院教授,而瘂弦則是編輯,這當然也影響他們的態度與立場。
瘂弦很早就是一位自覺甚高的編輯。一九六七年的信中他就說:「這一年來,我對當編輯這件事看得較以前嚴重,特別是到美國以後(當時參加了愛荷華國際寫作班),眼界寬了,覺得過去的一些作為不夠成熟,因此『文藝青年』的氣息,已不是像我們這樣年齡(當時三十五歲)的人所應該有的了。什麼事都要負責任,假若我是那刊物的編輯,不管主編協編,那刊物上的每一篇文章,我都應該負責任,否則,就是對文學不忠誠,就是對自己信仰的一種污辱。」
他具備一種特殊的編輯條件,那就是為作者著想,而楊牧一直都是他最為在意,最為用心著想的對象。因緣際會,瘂弦從一份同仁詩刊的編輯,跳到了救國團系統中,先是接突然自殺的朱橋編『幼獅文藝』,進而統籌「幼獅」品牌下的各雜誌,還接任「華欣出版」的總編輯。二度赴美到威斯康辛州立大學得到了碩士學位,本來說:「...為人作嫁的編輯生涯,似不宜再繼續,如果混張文憑,結束老編生活,在台北找個二、三流大學做個專任教員,閒下來整理一下自己的寫作事業,是為上策。」然而還沒回台灣就被網羅到『聯合報』,主持「聯合副刊」,加入了由高信疆在『中國時報.人間副刊』掀起的副刊競爭大戰,成了台灣這頁奇特媒體與文學、文化密切糾結歷史中的一方要角。
在編輯職務上步步高升,擔當愈來愈重要的角色,卻使得瘂弦要能實現能夠自己負責、終於文學終於信仰的理想,也就愈來愈難。
首先他必須面對『中國時報』與高信疆的強大壓力。他告訴楊牧的真切感受是:「現在我好像在馬祖前線,對面是高匪信疆,是年青富有衝力的悍將,我拚老命實在划不來,他是學生輩,本來以師禮待我,現在看這老漢要搶小老弟飯碗,他只有改以『瘂賊老弦』呼之了。」
當時文壇盛傳瘂弦視每天早晨翻開『人間副刊』為莫大折磨,害怕又要看到高信疆推出什麼意想不到的轟動專題,因此罹患了「懼高症」。兩家報紙副刊的工作人員甚至必須玩起「諜對諜」的拉鋸,己方有什麼重大企劃要嚴格保密,以求震撼對手;倒過來,也必須用盡管道想盡辦法去刺探對方會有什麼樣的新計畫、新花招。
如此創造了台灣副刊空前、想必也絕後的繁榮熱鬧局面,而瘂弦確實飽受壓力,以致在信中對楊牧恨恨地告狀:「高信疆此人最近常常罵我,用語粗鄙,居心惡毒,我已不把他當朋友了。我是一個善體人意的人,凡事替人著想,但對高,實在令我作嘔。能使我生氣、『記仇』的人並不多,我一向忍讓,但他實在太過分;為了效忠老板,忍心陷害朋友。」
不過三年後高信疆離職去美,瘂弦收回了原本的「記仇」,說:「他不做了,我也感覺空虛無聊。這六、七年雖然我與他也有玩惱的時候,但朋友總歸是朋友。這人太好強了...」可以重新認做朋友,然而瘂弦卻絕對不願再和高信疆當對手。瘂弦在籌辦『聯合文學』時,聽聞:「信疆他們也要辦文學刊物,真煩人。...本來我蠻有興趣的,一想到跟高信疆纏鬥在一起,就覺得瑣碎,沒出息,沒志氣,無聊。莊嚴、純粹的理想感都隨之降低了。當然,我辦我的雜誌,但高一來情況就會亂(這人我太了解)。這一年多我與金恆煒(當時的『人間副刊』主編)相處,真如清風明月,舒服萬分。其實都編得不錯,各有各的口碑,文學上的事,誰能把誰打垮?」
後來證明,『中國時報』和高信疆並沒有要辦文學雜誌,他們辦的是綜合性的『時報周刊』。沒有高信疆來攪局,瘂弦投入在『聯合文學』的理想感,卻終究還是落空了。其中最早澆他一桶冷水的,正是摯友楊牧。
『聯合文學』在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創刊,楊牧隨即寫了一封長信給瘂弦,在信中羅列出十七條意見,「...所說的全部都是批評性的話」。除了第十七點說:「我覺得作品的內容或作家的『陣容』並無任何突破可言。整個看來,絕對是聯合副刊的換裝改扮,不但內容路線如此,聯副見不到的新名字也幾乎完全沒有。」其他十六點都是針對『聯文』創刊號上刻意設計的版面文字或圖樣呈現。這充分顯示了楊牧的編輯觀念與非常堅持的風格:文學是嚴肅的,文學內容是自證的,不應該有太多干擾閱讀的補充或解釋,添加的花樣愈少愈好。
這樣的觀念與風格,相當程度上落實執行在洪範書店的出版品上,有助於洪範維持文學純粹性與品牌識別度,然而對於八0年代正走向熱鬧喧嘩的台灣雜誌,已經不切實際了。
瘂弦主持『聯合文學』的時間不到一年,即使還掛著「總編輯」的頭銜,一九八五年九月號的「編後語」已經不是瘂弦執筆的了。但瘂弦並沒有告訴楊牧這項重要的職務變動,引發楊牧在九月十四日寫了一封語氣感慨且帶有怨懟的信。
信中楊牧遲來地回應了前面提到批評無名氏的那件事。「...我們後來不能像從前那樣推心置腹交談。我怕說太多了便傷害你的感覺與自尊,你更怕引起我暴躁的情緒,所以總以最大的友愛容忍著我,或者說「應付著」我。我痛斥無名氏一案最可見你的苦心--我很感激,但也很傷心,因為即使天下人都以為我罵得公道,你前後對我的勸告證明你不以為公道必須爭取。你勸我為人為文要忠厚,但從頭到尾沒有談到『對』與『不對』的問題。」
這和瘂弦離開『聯文』有什麼關聯?楊牧的解釋是:「你有一顆溫暖和平的心,以為天下一切可以用容忍來斡旋,但你怎麼能保證天下人都和你一樣有那溫暖和平的心?在表面上你力能please everybody但英諺正是please everybody, please nobody,最後招致天下人不平的埋怨,因為人都是自私的,欲望都是無限的,而且大半文藝界的人都是盲目地以為天下第一的。你努力滿足大家的虛榮,努力在息事寧人,可是久之,這會使你失去個性與原則,而當一個像你這樣的地位的人,一旦失去個性與原則的時候,就是無以讓人傾服仰望的時候,則禍起蕭牆,最親近的人都可能反對你,出賣你,想踏過你去爭取他們自己的東西。」
『瘂弦書簡』中只能看到這年十一月十八日寫給楊牧的信,說:「很想寫封長信給你,但一直靜不下心來,每日應付完眼前面的一大堆工作,人困馬乏,回家只想睡覺。橋橋(瘂弦太太)去美近月,我也沒寫信給她(一個字也沒寫)。想起來心痛。」看來瘂弦並沒有正面回覆楊牧針刺般的表白,無從知道他的反應。
處女座的楊牧當然比瘂弦有個性有原則多了。他其實在編輯方面也有許多投入,這批書信透露了他對出版的心力付出。楊牧對於台灣文學出版最醒目的貢獻,是長年持續為洪範書店的書籍撰寫折口的介紹短文。現在我們知道了,他之所以能夠、也願意不署名地寫這種文字,那是因為這些書都經過了他的嚴格眼光挑選審核,他真正了解這些作者、這些書,是真正從編輯工作本位上生出這些精確且雋永的段落。即將出版的『楊牧全集』將首度將這些短文完整收錄,還其為楊牧作品的正當身分。
楊牧不只是詩人、散文家、學者,還要補上他編輯、出版上的努力與成就,才算鋪齊了完整的人生拼圖;瘂弦更是不能被侷限在編輯的角色上,他的詩作,雖然從頭到尾只有一本『瘂弦詩集』,卻已足為傳奇精品。而兩人書信中,多有對於文學創作的衷心信仰告白。
瘂弦說:「...學問也者,乃新品種的窮忙也,荒謬,沒有道理,無聊。想想當一首詩誕生時,什麼滋味比這更好,老實說,給個皇帝都不換。」楊牧說:「你到底寫了詩沒有?不要開玩笑,這是我們最值得驕傲的事,別的進步了,固然好,但是假的;只有寫了好詩,才是真榮耀真幸福。」瘂弦說:「..要做偉大詩人簡直不可以沒有學問。這次來美,這方面對我的刺激是相當大的。我在語文上吃了很大的苦,其中也有羞辱,我在班上有一種沉默的傲氣,漸漸地他們已知道我不簡單。我不太看得起他們,覺得他們赤足散髮,只不過是一個架勢,內裏是空的。」楊牧說:「黃用...我們意見分歧愈來愈大;他上次居然說:文學很『脆弱』、『不實際』...他已經不是詩人了,因為他認為詩的價值在生物化學之下,這是不可以的!」
一九六九年九月,楊牧接到瘂弦從愛荷華寄來的信,信中竟然附上了他在愛荷華進修一年的成績單。楊牧立刻知道瘂弦的意思:「你的學業成績顯然令人感動,這個成績一定花了你許多時間和精力,也難怪你沒寄詩來,寄了許多A來。」但楊牧終究還是要說:「好好寫些詩罷,再不寫詩,讀者都要把你忘掉了,你的心情也不會太好,這是很嚴重的。」
雖然瘂弦畢竟沒有寫出更多的詩,然而他和楊牧長時間護持著台灣的文學創作活力,不論是主觀的努力態度或客觀的成就,都值得後來者存記、感念。
文/楊照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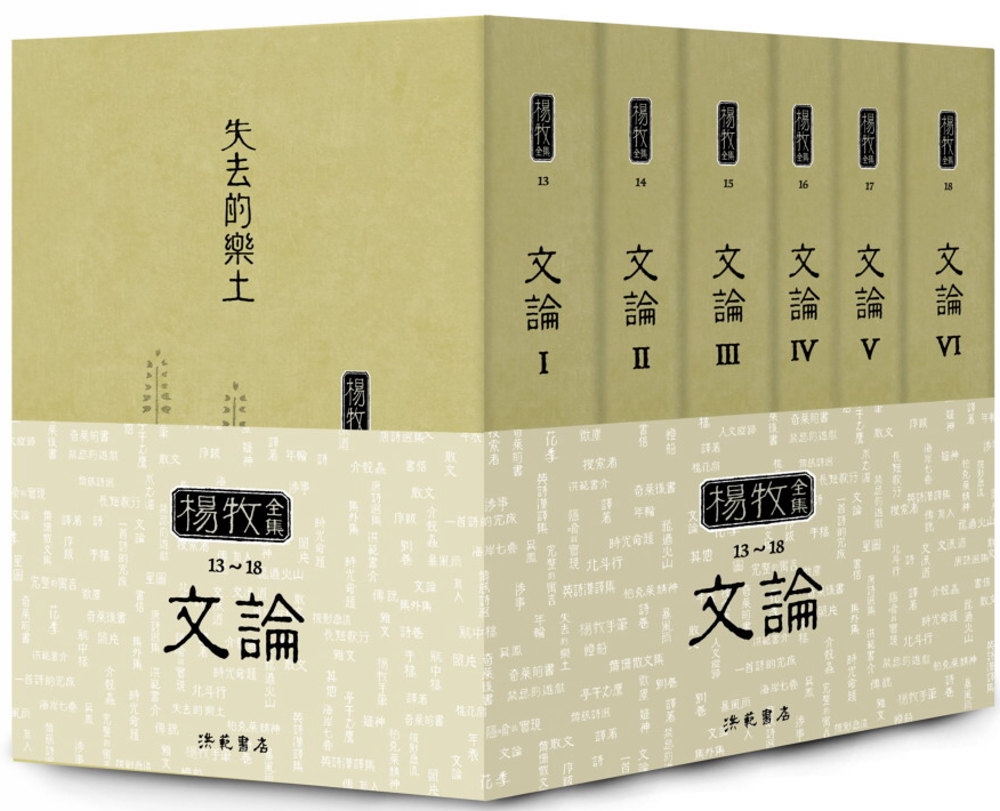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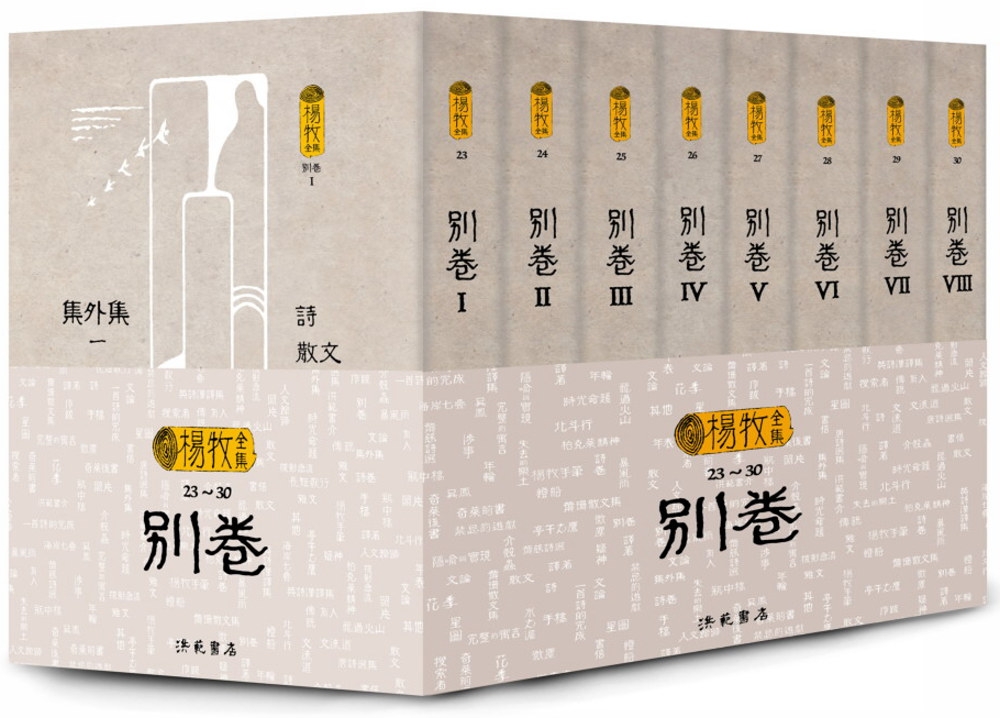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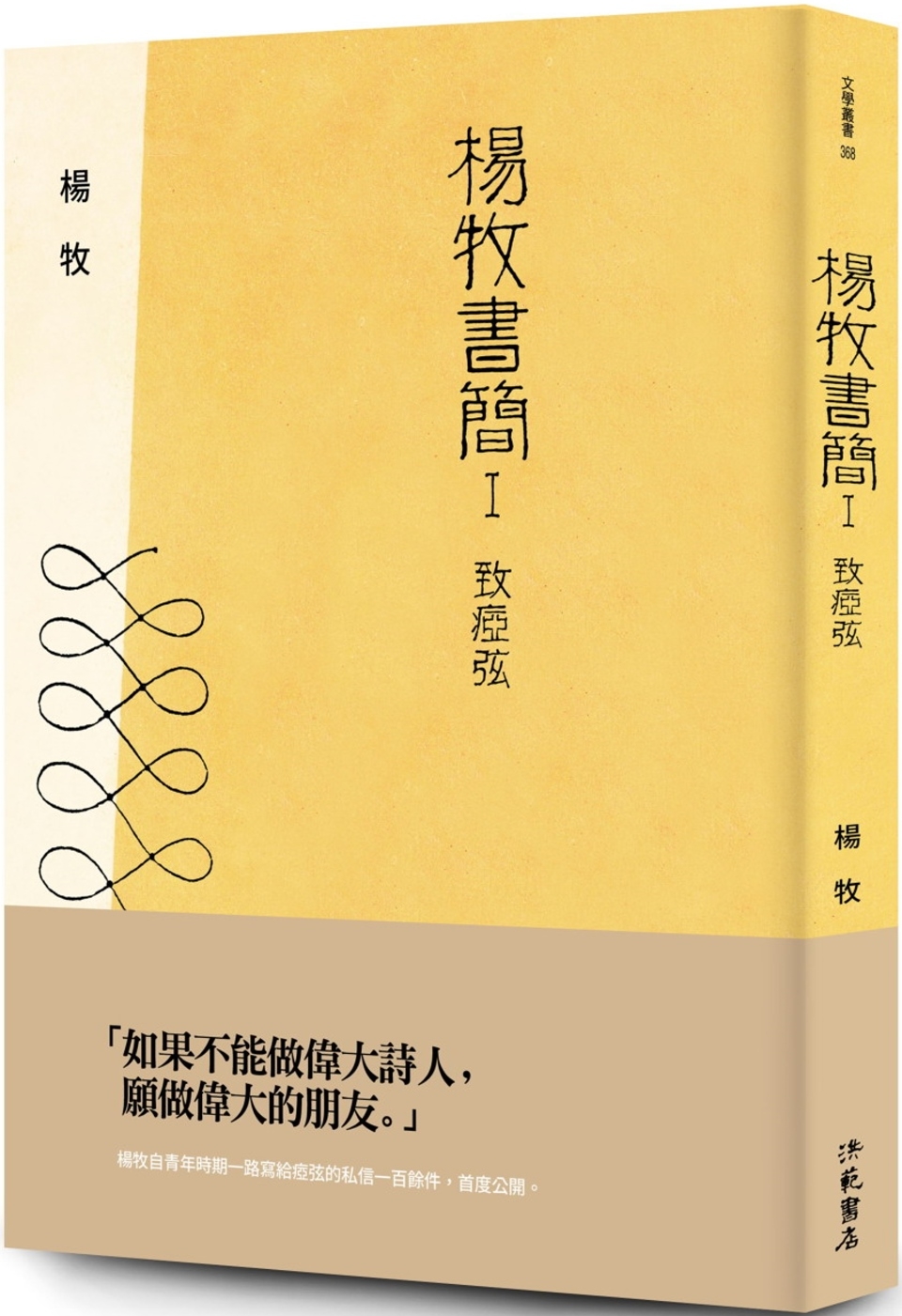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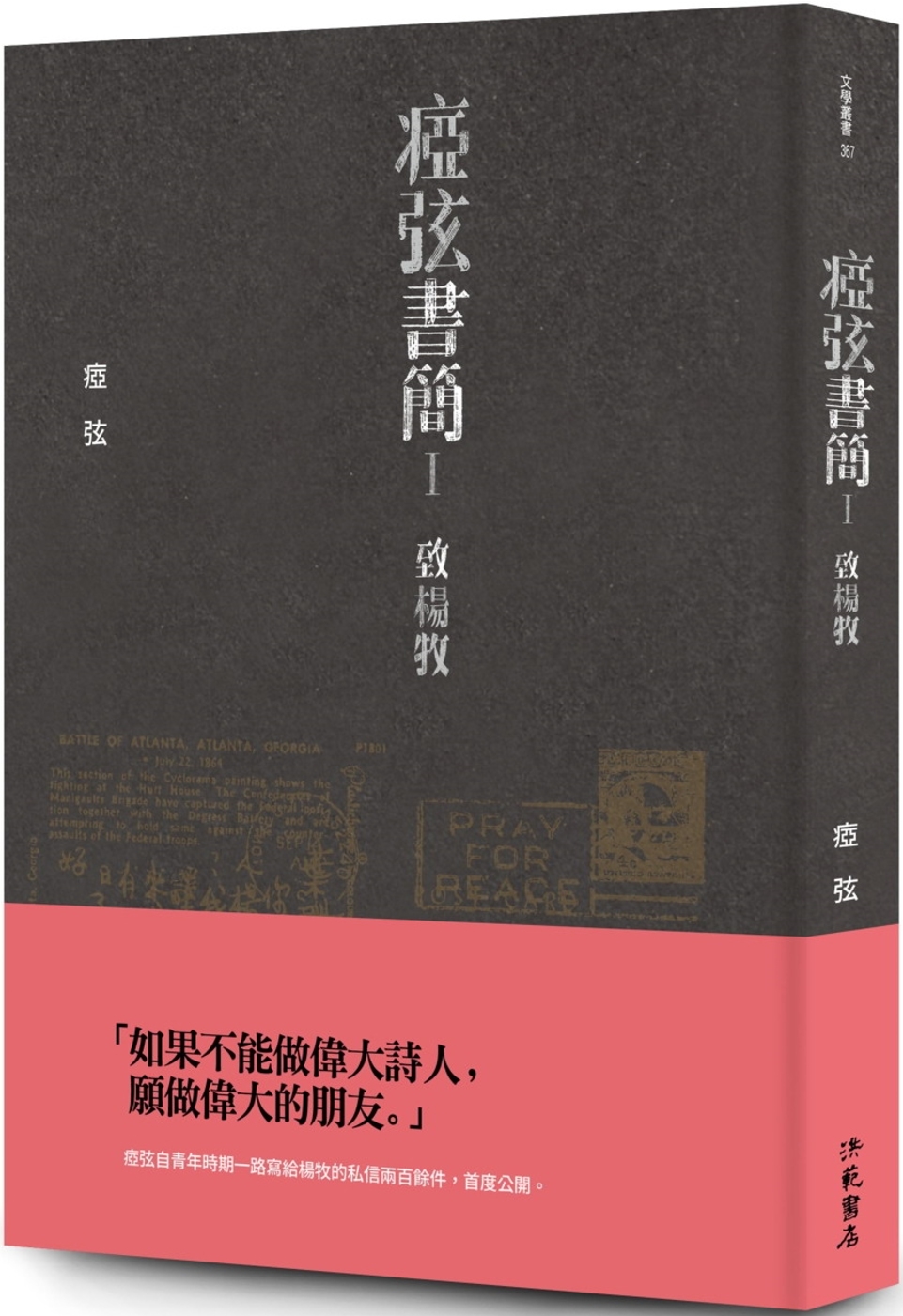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