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副總統呂秀蓮(1944-)也跟文學有緣。例如,她在獄中(1980-1985年)寫了小說《這三個女人》。赴美取得第一個碩士之後、再次赴美取得第二個碩士之前,她已經以《新女性主義》 等書著稱。政工幹校出身的符兆祥(1937-)在1976年出版《夜快車》(台北:文豪出版社),書末附有呂秀蓮執筆的〈評介「夜快車」〉。
呂的評雖短,卻透露多種訊息:一,呂認為符屬於上流社會(應指在國民黨內任職,而呂本人當時已經是國民黨的眼中釘),卻在小說描寫市井小民:呂很在意黨內外的跨界、階級的跨界;二,符描寫的女性不懂掌握愛情(而呂自謂「或許是我自己對愛情太過執著吧?」);三,符不崇洋(由此可推論當時台灣很崇洋──美國);四,符是外省人(海南島人),卻關心「本省籍的草地郎」──這是土生土長的呂最激賞之處。
呂文顯然不同於當時的主流序跋:她留心文本再現的社會議題(省籍差異、階級差異、性別差異等等),而非只是談天說情、打太極拳。
呂也注意到書中兩篇流風不同的小說。她寫,「由於流風的不同,〈新南陽拆了〉想寫同性戀卻沒有很明確地勾勒出他們的心態來,〈找顏色的女人〉一文亦有類似的遺憾。如果我們的風氣不適宜,或者作者本身不方便,我倒認為還是多把關注投給那一群默默的、無爭的、平凡的卻真摯的為數甚夥的市井小民要來得有意義;不知符先生以為然否?」

和John Gavin 主演),青年婚後偶然走過南陽街,發現電影院已拆,不免傷感憶及少年,但少年已移居美國。所以這個已婚男子在惦念甚麼?
也就是說,呂認為符因為「不適宜、不方便」而不能放手寫好同性戀,那不然就別寫罷,還不如寫真實的一般民眾吧。她的話有些問題:她才稱讚符寫了很多市井小民,怎又勸他多寫市井小民而不寫同性戀?另,同性戀者難道不真實、不屬於老百姓的一部分嗎?
但呂的話要放在當時脈絡中來看。時值1970年代,鄉土文學正在挑戰1960年代興起的現代文學。或許在呂眼中,鄉土文學寫市井小民,而現代文學寫了同性戀(如白先勇的短篇小說)。她不看好同性戀的原因之一,可能是為了一挫現代文學的銳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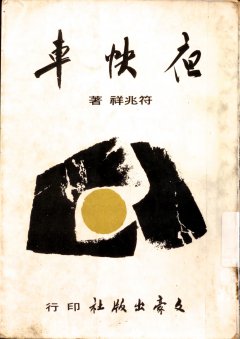
楊還輸呂一籌的地方,在於呂看出〈找顏色的女人〉寫了同性戀,但楊似乎沒留意這篇。這倒不能說楊眼拙,而該說呂慧眼:〈找顏色的女人〉沒有明言男同性戀,甚至還主打(讓男人飢渴的)女人,但它的確刻畫了男人對男人的肉慾。

這篇怪誕小說乃透過資淺男員工的眼睛,去看資深男員工怎樣被老闆的千金挑逗。伸手摸男體的人是千金,拚命看男體的人是新學徒:他眷戀的眼神凝視老學徒洗澡、裸體(全身、正面)、胸肌,對老學徒又愛又嫉,讓人聯想到王禎和的《美人圖》——但這篇其實早於《美人圖》。
〈找顏色的女人〉展現了女人垂涎男人和男孩垂涎男人的競爭;慾望女人的男人在文中不像一般文學作品中具有主導地位的主角,反而任憑女人的手和男孩的眼宰割。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比較文學博士。作品曾獲聯合報文學獎中篇小說首獎與極短篇首獎等。著有短篇小說集《感官世界》、中短篇小說集《膜》,以及評論集《晚安巴比倫:網路世代的性慾、異議與政治閱讀》,編有文集《酷兒啟示錄:台灣QUEER論述讀本》、《酷兒狂歡節:台灣QUEER文學讀本》,並譯有小說《蜘蛛女之吻》、《分成兩半的子爵》、《樹上的男爵》、《不存在的騎士》、《蛛巢小徑》、《在荒島上遇見狄更斯》等多種。現為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專任助理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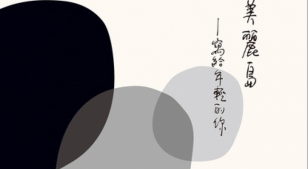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