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本書不是單純的考古學著作,書名《馬、車輪和語言》直接說明了本書的目的是借助馬的馴化、車輪的發明而分析古代文明的載體——「原始印歐語」——何時出現,在哪裡出現,由誰來講,以及如何擴散?
富察:
這真的是本書最有趣、最具挑戰性、也是最有價值的地方,作者正面挑戰一個西方二百年來爭論不休的話題──「原始印歐語言」的建構是否可以成立?又該如何驗證其出現的時間,及「原鄉」位置所在?這個爭議不只是單純的學術問題,而是牽涉到文化及國族建構敏感神經的政治問題。
育誠:
我個人最感興趣的是本書作者對語言和政治之相關性的分析。因為自從18世紀威廉·瓊斯爵士提出印歐語系假說以來,就遭到各種挪用及扭曲,最具代表性的便是納粹德國時期的「雅利安人」國族神話。
「雅利安人」一詞出自梵語,意指「高貴的、光榮的」,具體指涉的是印度種姓制度中的統治階層,即駕馭馬戰車的印度征服者。因此,當梵語及印度文化透過語言學與歐洲文化產生了直接的聯繫,「雅利安人」便與「印歐語族」逐漸畫上了等號。「雅利安人」恰好滿足了各方的想像,種族—語言—國族三位一體的觀念應運而生,而最終這釀成了人類社會的巨大災難。
富察:
但擊碎日耳曼文化優越論者國族神話的研究表明,「原始印歐語」的原鄉竟然不在古歐洲,而在西方文明視之為野蠻地帶的歐亞草原,在烏克蘭或哈薩克一帶,這一結論對於西方學術界和文化界確實是巨大挑戰。但我想斯拉夫考古學界心裡會很爽。或許我的共產主義/社會主義教育背景,我在編輯本書時很敏感的注意到這位美國的人類學家在採取斯拉夫草原考古學界的部分學術觀點時,內心會如何回應西方考古學界的種種質疑。冷戰結束之後,斯拉夫考古學界和英美西方考古學界之間出現了對話與融合。或者可以說,如果冷戰持續至今,那麼這本書依舊無法寫出來。
育誠:
你的這種分析角度,我這個地道的台灣人很難敏銳感受到。但作為台灣人,我最感興趣的地方是,作者進一步指出,「原始印歐語最初之所以傳播至東歐大草原以外的地區,主因不太可能是有組織的入侵或一系列的軍事征服」。對應到台灣,我馬上想到的是南島語族向太平洋島嶼的擴散。
作者認為,原始印歐語的傳播,更得益於聚落間基於互助合作所形成的聯盟,而非軍事征服。雖然無法完全避免劫掠和暴力,然而,這些草原族群之所以能夠成功地定居,更重要的是他們社會制度與文化的包容性(透過『庇護人─附庸系統』的賓主關係,將他者也納入權利和庇護下)。換句話說,外來者並非征服者,而是透過「協商與契約」與本地者形成的新的共生關係,最終融合成新的文化。
富察:
本書舉了一個有趣的具體案例:英語中的「賓客」(guest)和「主人」(host)是有著相似詞彙結構的同源詞,從原始印歐語的字根(*ghos-ti-)衍生而來,這顯示了原始印歐語族的社會規範非常重視「賓主關係」。我們甚至在印歐語族的遙遠後代──以古希臘語傳唱的《荷馬史詩》中依然可見:兩位敵對的戰士在得知自己的父祖輩曾建立「賓主關係」,便立刻停戰、言歸於好。
育誠:
在編輯此書的過程中,我真的常常想到台灣的古老文明是如何傳播和擴散的,不僅僅包括南島語族的文明,也包括當下台灣的主流台語文化是如何跨越海峽而來,以及如何植根在地。
富察:
這也是我們出版本書的動機之一,「外部視野、在地關懷」是八旗出版的DNA。最後我也要提醒讀者,沒有任何一個單一因素能夠有效地解釋「印歐語族」的擴張,不論是種族、社會性因素(如人口壓力)或所謂「精神」及「命運」。語言或文化的傳播需要交流雙方的積極互動,而非征服與統治。這樣的觀點不只成功的消解了傳統解釋印歐語系擴張的軍事征服傾向,更提供了一個思考世界史與文明演化的全新角度,這是本書值得推薦之所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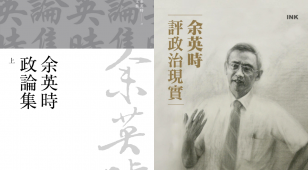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