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柳浦善(文學評論家,群山大學國文系教授)
自殺,或者現代性的鏡子
金英夏的《我有破壞自己的權利》是一部非常陌生和奇怪的小說。這種陌生和奇怪首先來自書中的人物以及人物之間的奇異關係。
出場的人物與「現實的規範」發生了實質性的決裂,而且每個人物都不例外。其中有個非常惹眼的人物,也就是可稱為「自殺嚮導」或「自殺承包人」的敘事者,他專門捕捉隱藏於現代人內心深處的死亡衝動,如果他從某個人身上發現了隱祕卻強烈的衝動,就會毫不猶豫地勸說對方選擇英雄而濃縮的生活,即自殺。如果對方做出了勇敢的決定,他會幫助對方安全而準確(?)地壓縮自己的生命。這樣的人物很難找到先例,正是這些陌生而奇怪的人物,使得本書變成了陌生而奇怪的作品。
並非只有「自殺嚮導」顯得怪異,其他人物同樣與當前的社會規範之間有著深刻的裂痕,只是程度不同而已。比如,有人不去參加母親的葬禮,卻跟女人做愛;有的女人勾引情人的哥哥,當然這個哥哥同樣很奇怪,他接受了女人的誘惑,最終形成了兄弟二人共同享用一個女人的局面。對於決心自殺的女人,他不加勸阻,只是反覆觀看收錄女人身影的影片。小說中還有這樣的女人:她每次喝精液的時候都要用水漱口,後來只要喝水就會嘔吐。書中不僅充滿了這種「不在規範之內」的人物,而且作者又藉由生活中正在發生的事情讓這些人物形象化,因此這本小說讓人感覺陌生和奇怪也就是理所當然的事了。
但它之所以怪異,終極原因在於「把這些規範之外的人聚集在一起」的敘事原理。《我有破壞自己的權利》的部分和整體結構、人物彼此的關係、描寫和敘事的核心,即在於前衛且大膽的挑釁。它把人類最高的權利定義為「破壞自己的權利」,即自殺的權利。也就是說,每個人都有破壞自己的權利,只有行使這種權利的人,才能成為真正的人。「我不想戰死,我要死在我想死的時候」,針對這種將自殺昇華為藝術,讓人聯想到達達主義的問題,小說就從現實的角度做了全新的闡釋。也許在對現實進行深入的省察之後,得出了自殺是人類僅有的自尊的結論。
無論是出於何種情況,《我有破壞自己的權利》終究把自殺歸結為人類可以選擇的真正的實踐方式,並且透過這個稜鏡觀察社會,藉此描繪了極具反諷意味的現實。按照書裡的說法,儘管現實生活中的人們都是有生命的存在,然而他們正在走向死亡;儘管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執著而強烈,然而關係內部卻是空白的。小說冷靜而不帶感情地刻畫了這樣的現實,足以讓讀者感到恐懼。過去遭狹隘的幻想體系掩蓋的存在,在本書出現後得以回歸,這個恐怖而頗具誘惑性的存在,就是現代社會的孤獨、頹廢和倦怠,以及由此引發的性欲和死亡衝動,這些在小說裡的描寫極有說服力。
《我有破壞自己的權利》出現之後,韓國文學開始朝著截然不同的方向發展。借用雅克.德希達的說法,「所謂未來,就是與已確立的規範徹底決裂。因此,未來只能在某種怪異之中預言自身,並且自行呈現」 。也就是說,這本小說的奇怪之處可以看作是某種先兆,提前預知了即將呈現的未來。有位眼光獨到的評論家早就這樣評價了金英夏從《我有破壞自己的權利》開始的小說,稱其為「明確體現了時代裂痕的小說」 ,這樣說絕對不是誇張。這部小說已經事先決定了後來出版的小說的命運。換句話說,我們可以把《我有破壞自己的權利》看作後來小說的源頭。
死亡的舞臺化和現代主義的回歸
《我有破壞自己的權利》「始於對兩幅畫的描寫,終於對兩幅畫的描寫」 。裝飾小說開端和結局的兩幅畫是《馬拉之死》和《薩達那帕勒斯之死》,也就是說,故事開始於對死亡的描述,同樣結束於對死亡的描述。很容易就能看出,這是一部關於人類永恆的他者——死亡的小說。如前所述,這並非普遍意義上的死亡小說,而是經由「主體決斷」的死亡,也就是與死亡屬性稍有不同的自殺。它講述的自殺既象徵了人類的有限性,又可視為人類無限性之展現。透過這種兩可意味強烈的死亡形式,小說以傳統方式再現了當今社會的真實存在。

《馬拉之死》和《薩達那帕勒斯之死》(圖片來源 / wiki)
《我有破壞自己的權利》展示了死亡,以及死亡史之所以重要的原因,但是這裡提及的原因,不同於我們的預想和期待。書中並沒有透過哲學理論證明死亡為什麼如此重要,而是以同義反覆作答。死亡為什麼如此重要?很重要。只要你做到冷靜而不帶感情,就能透過死亡,透過死者的神情發現重要的線索。換句話說,死者之所以重要,也只因為他是死者。做到冷靜而不帶感情吧,這樣就能看到了。
故事以這種方式把死亡史提升為歷史的總結,也可以說這本書把全部人類歷史變成了「死亡的舞臺」,提出了「壓縮美學」。「不知道壓縮的人是可恥的。無可奈何地延長自己卑微的人生,這樣的人同樣可恥。不懂壓縮美學的人至死也不會知道生活的祕密。」敘事者稱頌壓縮的美麗,然而並非所有的壓縮都美麗。例如,敘事者喜歡閱讀旅遊指南,原因很簡單,因為「旅遊指南簡潔明快地壓縮了複雜的事實」。然而問題並沒有這麼簡單,每個城市都有數十萬生命和數百年歷史,壓縮方式肯定也數不勝數,問題在於這種簡單明瞭的壓縮,究竟能多準確而豐富地再現物件本身?假如這種壓縮未能準確而豐富地再現被壓縮的對象,那麼,也許它依然美麗,卻勢必伴隨著暴力和恐怖。
因此,說明壓縮美學,最重要的不是壓縮本身,而是說明壓縮的方式和壓縮的客觀性。但是小說裡的敘事者卻沒有考慮這些問題,他只是把全部人類歷史區分為「壓縮人生」和「卑微人生」,並且拋出「哪種人生正確?」的提問。不僅如此,這種分類還不動聲色地擴大到自動壓縮(也就是自殺)的「美麗人生」,和無所事事苟延殘喘的「無恥人生」。問題又出現了,你要過什麼樣的生活?這不是問題,而是強迫選擇。儘管這是兩選一的問題,然而供選擇的答案只有一個。於是,《我有破壞自己的權利》從壓縮美學不動聲色地跨越到自殺倫理學的範疇,這個過程是飛躍的,因為壓縮的人生同樣無窮無盡。壓縮的人生並不單純意味著物理時間的縮短,還得考慮到這是否為有意義、有價值的美麗人生,比如為歷史獻身,為他人而犧牲自己,或者創造前所未有的新的真理體系。但是,《我有破壞自己的權利》沒有考慮這些,只是把「壓縮人生」限定為破壞自己的權利,敘事者借助莎士比亞的「死亡光顧我們之前,我們首先衝進祕密的死亡之家」,把自殺說成是盡善盡美、至高至純的美麗。
本書認為此時此地的人生只是卑微和荒誕生活的簡單重複,的確有其可能性,但是從壓縮美學過渡到自殺倫理學的過程中仍然存在著飛躍,這部作品就是透過這種邏輯性的飛躍,完成了特有的自殺倫理學。
透過特有的選擇和集中,也就是透過徹底的排除和隱藏,《我有破壞自己的權利》把人生的重要領域——死亡問題引入了整個韓國文學。這部作品之所以令人驚歎,並不僅僅在於死亡或自殺問題的回歸,而是不但復原了自殺問題,也復原了促使自殺倫理學產生的現實條件;具體說來,也就是現代社會的孤獨、倦怠和頹廢,以及由此產生的對於物質似是而非的渴望。南北分裂等韓國特有的意識形態早已被驅逐到非主流範疇,而這部小說將其重新復原到我們的生活。
對他人的關照和倫理主體化道路
不過,對於自發性死亡的禮讚並非這本小說的全部內容。除了禮讚抵抗冷漠現代主義的自發性死亡,書裡還有別的東西,那就是對於自發性死亡的批判態度。本書不僅讚美自發性死亡,同時也保留了批判的空間,尤其是小說的後半部分,這種對於自發性死亡的批判態度就越發明顯了。透過故事開場對自發性死亡的讚美,不僅小說裡頭,甚至我們整個社會都變成了自發性死亡的盛宴,成功排除了跟社會的希望與發展相關的言論,製造出「被永恆時間操縱」的社會。但到了後半部分,小說卻開始執著地探討新的問題了——即遺憾的現實不動聲色地將現代人逼進「自發性死亡」的處境,那麼我們能夠選擇的有意義的出路究竟在哪裡?這麼說並不意味著小說的整體風格不統一,或存在結構上的缺陷,在小說中,這種中心移動,是隨著看待物件的視角差異自然形成的,這是本書的重要特徵,與結構的斷裂無關。這種從對破壞性死亡的禮讚到批判態度的自然轉換,反而成為提高本書之破壞力的原因。
如果小說從頭到尾都極力讚美「破壞自己的權利」,也許會因為痛徹批判了管理且規範日常生活的社會,而讓人感到無比痛快,卻有可能覆蓋重要的課題,反而無從探尋突破嚴密監視體制內部的方案。但是,小說並沒有輕易陷入辛辣批判帶來的快感,在機智地闡明這個社會的本質就是全體成員都過著同義反覆的生活之後,又從容地探索這個事實帶給人們的不幸,和突破不幸的可能性。
小說最後走向自發性死亡的人物是兩名女性。她們之所以決定壓縮自己的人生,是因為自認為繼續生命之路只會成為卑微生命的延續。換言之,她們真正想要的是每天都有變化的人生,也就是穿梭於「既存規範內外」的豐富人生。小說裡,她們確實需要這樣的人生,而且不斷向其他人物傳達自己的需求,但是,C、K和敘事者始終對她們的需求置若罔聞。他們的置若罔聞最終把兩個女人逼迫到絕境,她們最後走向自發性死亡的原因,就包括這些人的冷漠。具體地說,他們對女人的迫切心願充耳不聞,或即便聽見了也不理不睬。小說準確捕捉了他們複雜的內心風景,同時也對他們以及生活在當今社會的我們,進行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分析。
《我有破壞自己的權利》藉由尋找逼迫柳美美和朱迪絲走向死亡的原因,呈現了小市民的冷漠(對別人漠不關心、以自我為中心)。這使得人與人之間無法達成真正的交流,同時也把全體社會成員的生命變成了同義反覆。根據書中的邏輯,不管遇到什麼人,結果都是重複著同樣的狀況。K總是試圖躲藏進壓力裡,以迴避與他人交流;C透過自己塑造的形象觀察對方,得以從每個人身上發現朱迪絲的影子;敘事者則從全體現代人身上讀出了死亡的衝動。這種「反覆」,把他們變得非常危險,他們也會遭遇兩個女人死亡時遇到的信號燈。「為什麼走了那麼遠,還是老樣子呢?人生這東西啊。」
由此看來,《我有破壞自己的權利》中的人物就是生活在當代的我們的自畫像,包括選擇自發性死亡的人物、逼她們進入這種狀態的自殺嚮導。我們常常虛無地依賴於大他者(Other)的規範,單方面地被他人牽引,或者封閉在虛構的幻想體系,拒絕和忽視與他人溝通,冷靜地生活於世界上。所以,我們既是朱迪絲和柳美美,同時也是C,是K,是自殺嚮導。如果我們繼續這樣在喪失主體的狀態下生活,早晚也會遇到存在於我們身邊的自殺嚮導,也許我們被他們牽引到死亡門檻,還會再回到原處,也許,我們就那樣了無痕跡地消失了。
(本文原載於韓國版《我有破壞自己的權利》)
延伸閱讀
- 【專訪】「我堅信,個人身體的權利屬於個人。」──南韓小說家金英夏談《我有破壞自己的權利》
- 【特稿】崔末順:抒情破壞與當代感性──韓國「新世代文學先行者」金英夏及其小說
- 【書評】石芳瑜:要麼創作,要麼殺人──金英夏《我有破壞自己的權利》的暴烈與頹廢
- 【韓文版編輯現場】從挖掘文學獎新秀到規劃系列作,我們如何打造「金英夏熱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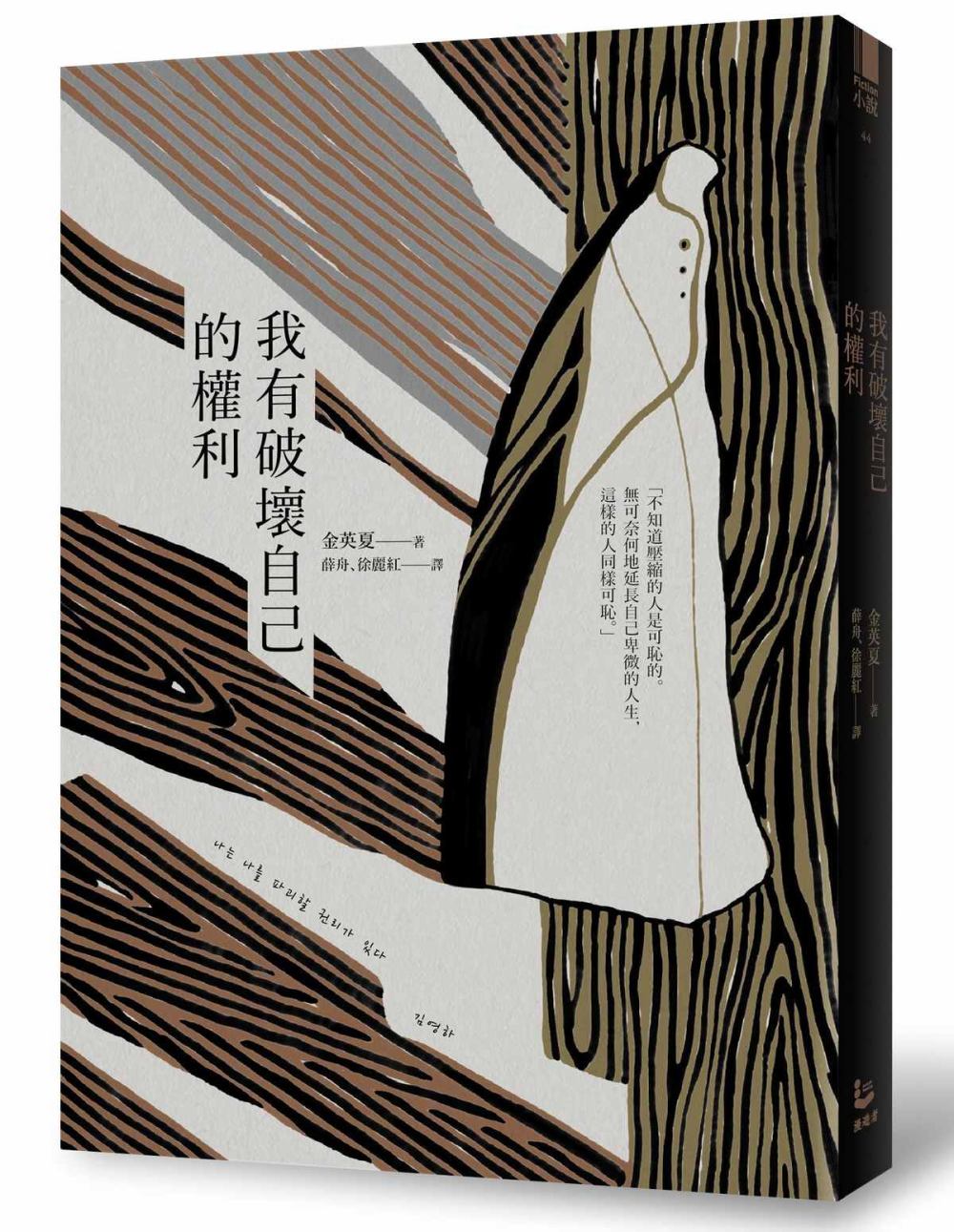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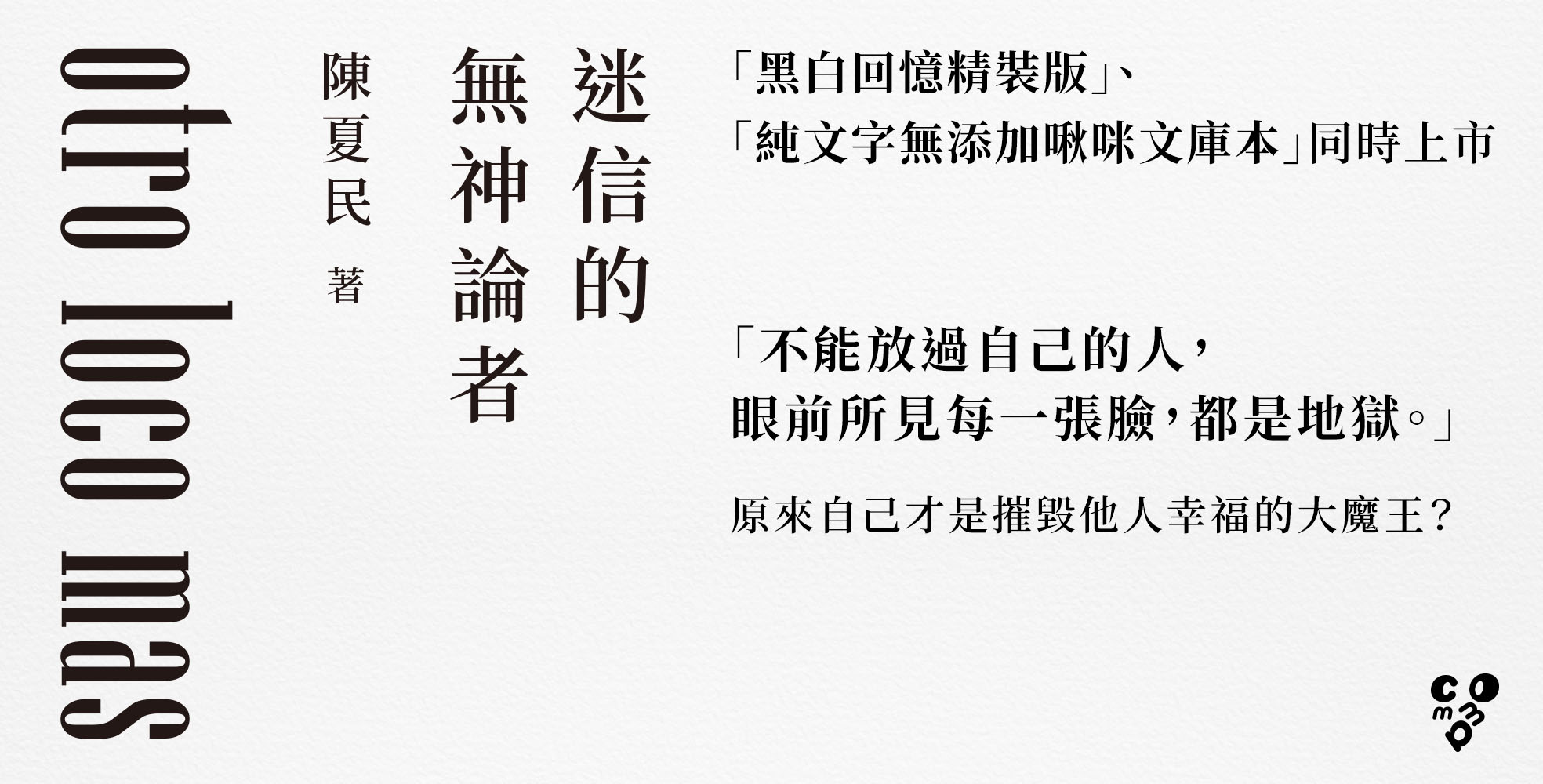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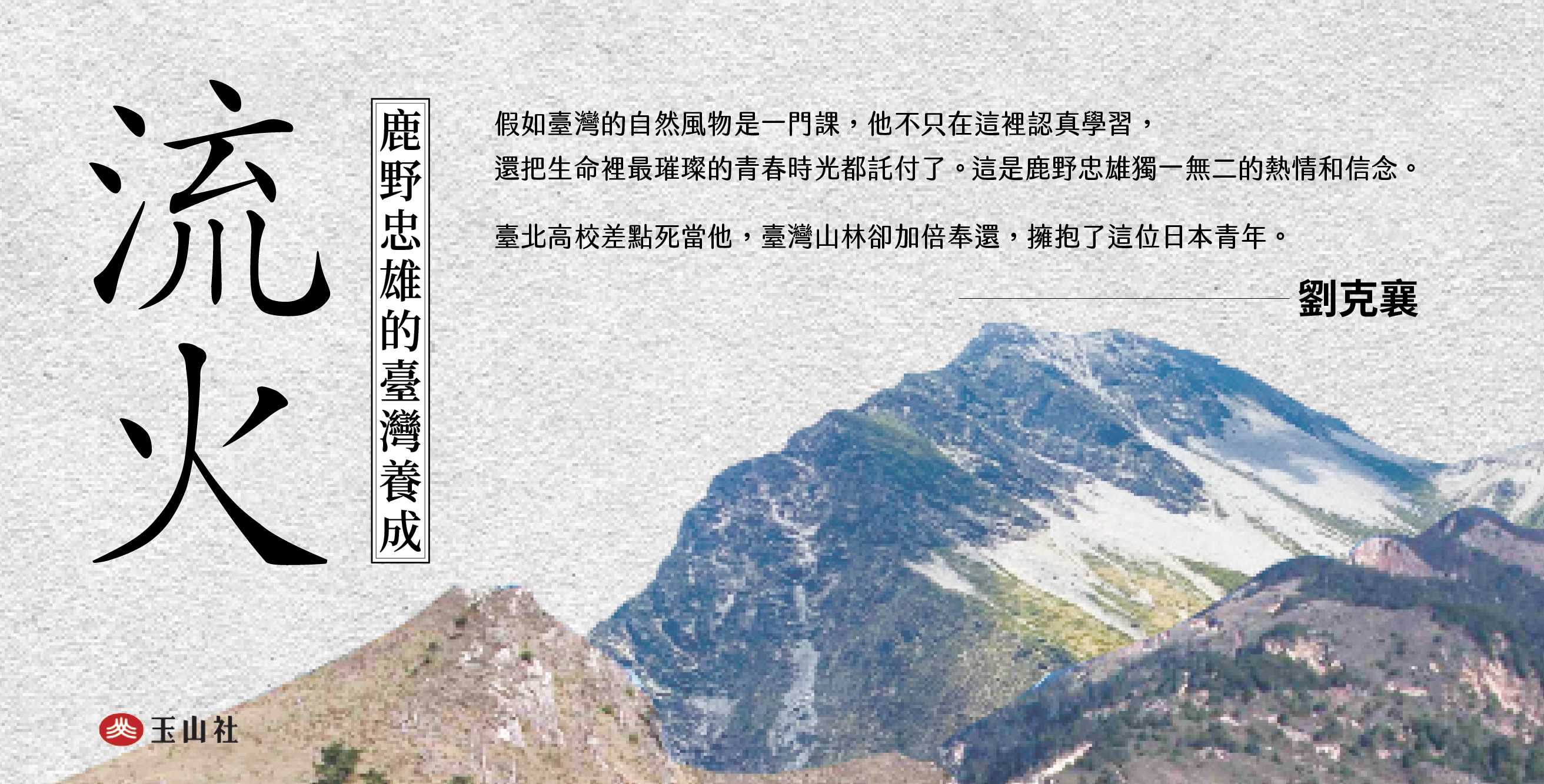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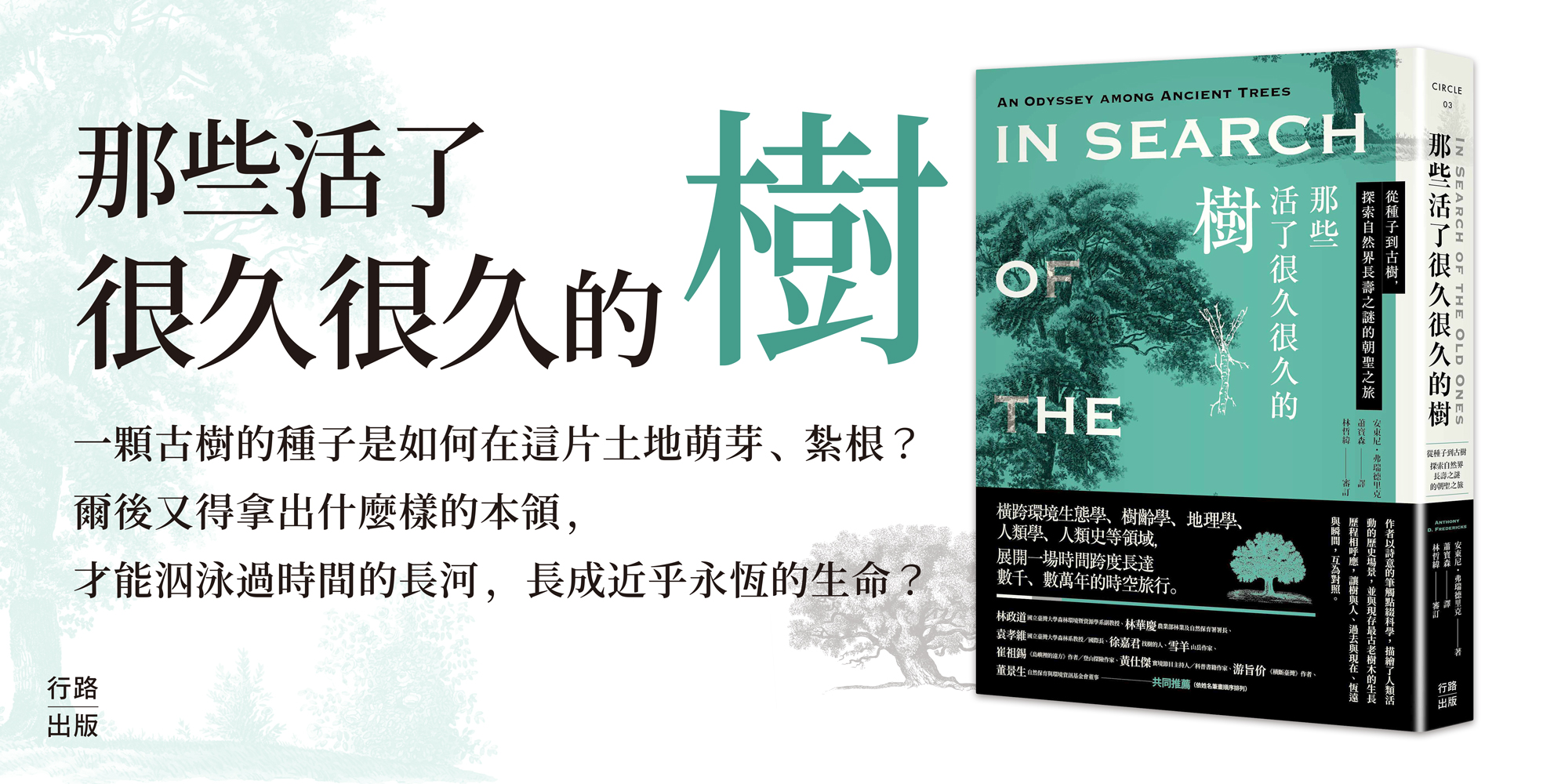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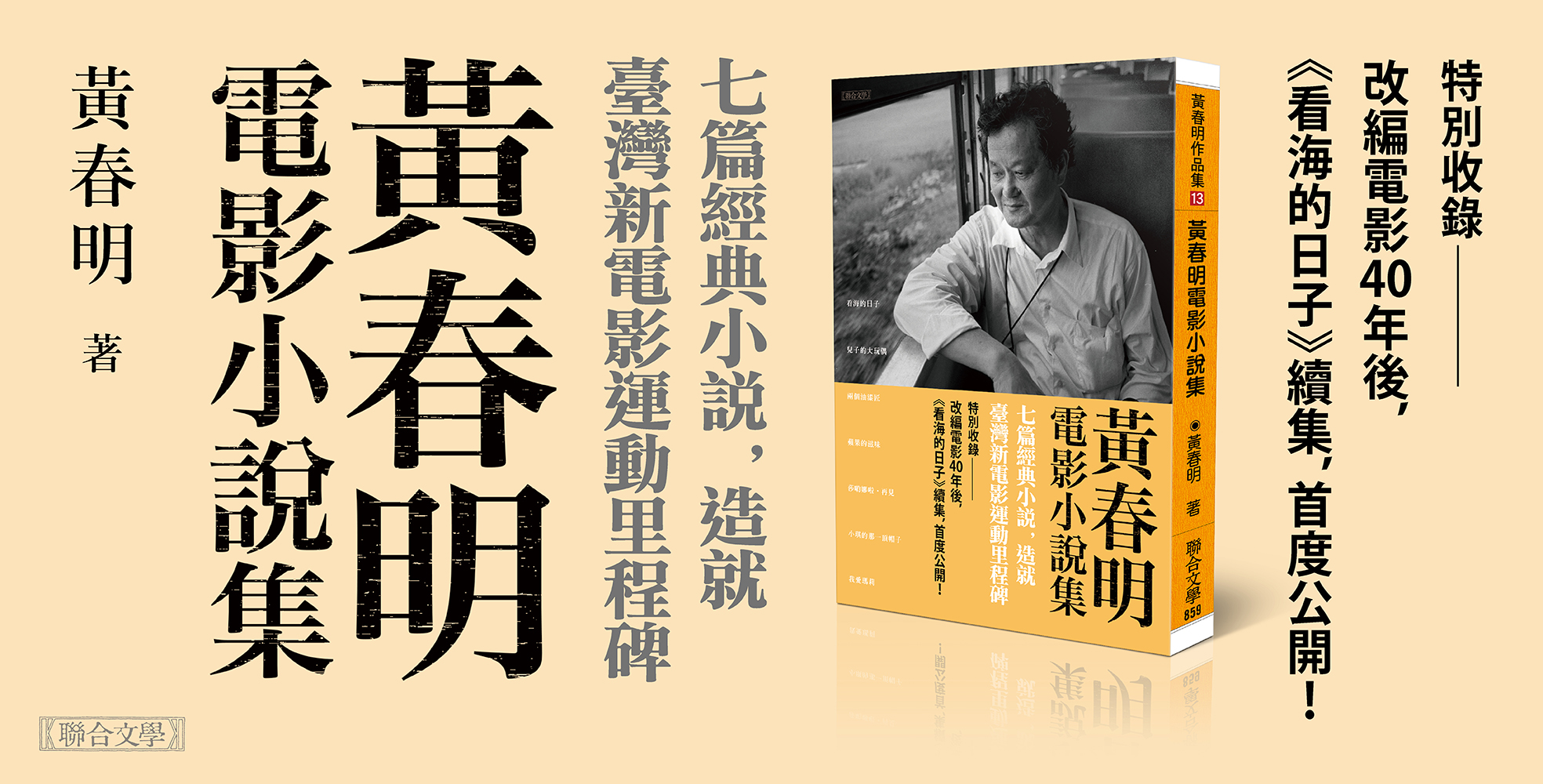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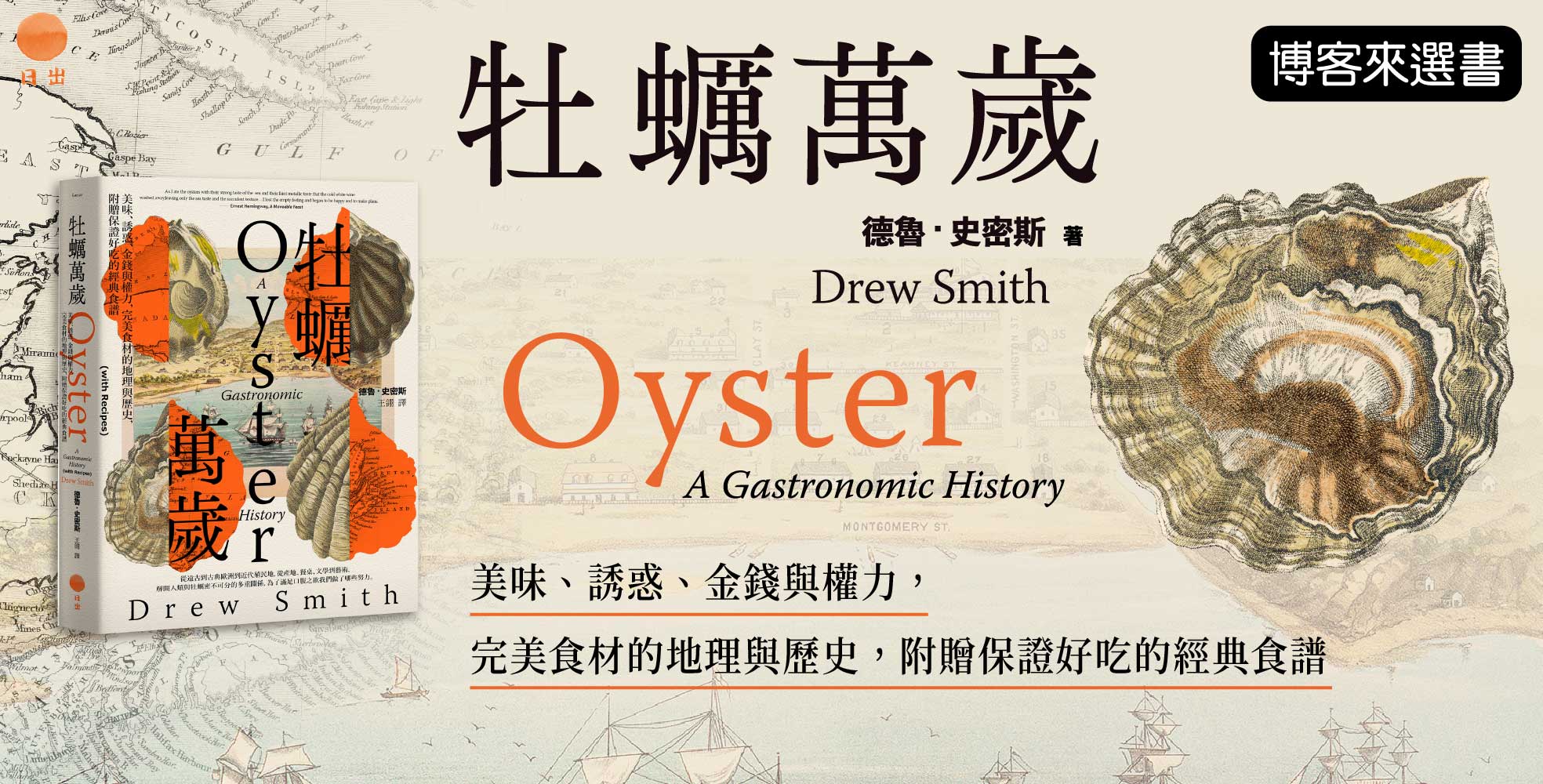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