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打開人性顯相室,我們可以看到似曾相識的自己,
解開只封存在記憶中的世界殘影,
讀取種種人們暗示的訊號回聲,劃下尚未結疤的傷痕,
拍打起角落裡累積的記憶塵灰,
這是我們身處的大世界,也是我們受困的小房間,
眾生內心在這裡顯相,紀錄妖魔天使齊聚一堂的人類樣貌。
 《一一》像是台北人集體的一場夢,浸泡在前朝的夢,諷刺地殘餘民國的海派習氣,自己與故鄉意識與特徵都不明,想跟著美國的榮光亦不可得,即便是社區裡出現幾位建中、北一女制服的身影,如今連帶教育的摧枯拉朽也失去了風采,《一一》告別了我們自以為曾有的階級,自命的小布爾喬亞,是上一代台北人逐漸遠去的回眸身影。
《一一》像是台北人集體的一場夢,浸泡在前朝的夢,諷刺地殘餘民國的海派習氣,自己與故鄉意識與特徵都不明,想跟著美國的榮光亦不可得,即便是社區裡出現幾位建中、北一女制服的身影,如今連帶教育的摧枯拉朽也失去了風采,《一一》告別了我們自以為曾有的階級,自命的小布爾喬亞,是上一代台北人逐漸遠去的回眸身影。
有一種人類的安靜是這樣的,菜市場的鼎沸人聲依然、咖啡座裡姊妹淘的笑聲不絕、家長的管訓聲時不時冒出、街角小黃狗仍然吠著陌生人,但你知道有些話題提出來會令人啞然,像破壞的某一個設定,是人們都約好的項目,外界看似路遠天廣的,但誰都知道「制約」就清楚地在前方,於是你知道那安靜是沉沉的瀝青色的,每晚朦朧間才可能隨著菸酒一塊不知所云。
《一一》清楚地拍出某一代人精神上的不自由。拿著成功當藉口,讓人忘記它的無法被定義。
「我們是不是只能看到一半的事情 ?」電影中,男孩洋洋在車上跟父親NJ提問,無法馬上得到父親的回答,人們魚貫地進入夜色中,在80年代時,現代化的道路是如開上高架橋一般,是沒什麼好遲疑的。
但那時候電影與戲劇上演的痛苦都是異常濃烈的,婦人攔轎喊冤、林投姐的悲歌、為愛求生求死、小媳婦的隱忍,母親一病送走孩子,自己的煩惱則像上了麻藥一樣,放在戲劇的淚海裡,自己的疑問反而顯得過輕而沉甸甸。
那時空標註的是你怎麼跑不出去的唯一價值觀,你每天看著一班班飛機送傑出或有錢學子飛往他們心儀的美國,沒有人能拒絕希望的大目標,即使那事後看來只是哪個神信手伸出的五指山。
因此吳念真飾演的NJ直到中年去了日本,才能稍稍鬆口氣地告訴初戀女友當初分手原因,「我那時考上電機系,你跟我父母都很開心,你們都不知道我的心是如何在揪與翻攪著。」在80年代,台大電機系形同於考上狀元般,符合國家產業發展方向,如一紙成功保證書,此時NJ原本的藝術興趣根本不被考量,眾人的期待就這樣壓了下來,沒人問他要什麼。
只要讀好書就沒事了吧?他女兒婷婷跟周圍鄰人也都如此看著自己這身綠色制服,以前這在社區中總是榮耀。
讓人想到,美國作家舍伍德.安德森寫的「使人變畸人的,便是真理。」這句像是古早從巷子裡吹來的一陣風聲,然而因真理而成為畸人的,無法改變自己的宿命。
如同男孩洋洋在電影的最後告別外婆時說:「我要告訴人們他們不知道的事情,看到他們看不到的東西。」這像是導演楊德昌自己許的心願般,他生長的那個時代,是就算看到另一面都無法說出來的,說出來的像破解了什麼騙局一樣,會被視為畸人,但畸人小時候並不會知道自己不同,只是慢慢發現大人認同的「正常」,就只是像每人都被發了一張複寫紙,強迫每個孩子描出一模一樣的世界樣貌。
如果看到另外一面,你就再也描不出他們所要求的「正確」,那正確是非常濃縮且矩形方面的,儘管世界天高地闊,你卻是金絲雀有著意識中的牢籠,無法留有迷宮給你探尋,你要當一個看似很好的孩子,或是看似像小太保?
 每人都被發了一張複寫紙,強迫每個孩子描出一模一樣的世界樣貌
每人都被發了一張複寫紙,強迫每個孩子描出一模一樣的世界樣貌
從瓊瑤的三廳電影、到後來《小畢的故事》,到楊德昌電影中的少年少女,年輕人的動線走來走去都是家裡客廳與回家的路上,年輕人是軍訓課下延伸的產物,環境看似沒有汙染,沒有令人滯悶人口密集,但卻始終有一種透不過氣的保鮮膜氛圍,年輕孩子包著那保鮮膜,讓他們看似前程似錦、一塵不染,唯一的想像是在海邊近似誇張慢跑,這樣的大人俯瞰視角,就是布爾喬亞對下一代的眼目探詢,令人想起80年末「寵物店男孩」樂團的〈西城女孩〉,MV裡照著櫥窗裡優雅的少年少女娃娃們,美好得令人窒息。
《一一》明明樹木綠地都在,卻無法給人自由的想像,無論NJ還是他兒子,就算有任何浪漫與詩意的念頭,就只是剪一小角似的,且必須藏在別人看不到的角落,如電影台詞:「藝術是無用的」。那是一個非常講求現實感的世界,不由分說地砍下與抽象世界的連結,其他被視為風花雪月的,是在現實中寄生了般,插朵花一樣不自然,不然就像楊德昌這類硬從這樣堅固的水泥縫中生出果子來。
電影中的時空其實並不遠,我們還能用目送的距離看著他們,然而我們就算想進也進不去了,因為那裡是借來的「美國夢」黃金殘篇,那時台灣當不成美國人,就跟他們借來一點生活觀、價值觀,無論唱的、聽的、說的都像點美國人,但我們也不會有他們尊嚴拉扯的失落,因為我們做的夢是假的,在台灣這島上假寐美國的夢。
代工業一衰退,以往能從日港抄的點子,一旦不能抄襲了,我們的美學就這樣沒打底地垮下來,因為從頭到尾都沒這塊,像個小康家曾做了一場大戶夢。
電影一開始的婚禮發生在圓山飯店,紅得如舊時代附身的場景,在楊德昌的視角與色彩中,你可不能說喜氣,只看到時間的塵屑飛舞,大人們在裡面辦西方婚禮,不和諧的各種元素搭襯,即使是大日子,過的日子也是這麼囫圇吞棗的,猛塞了什麼,也就消化不良的跟這城市一樣總半新不舊。
電影中找不到存在感的中年角色們,在明確的成功規則中長大,而規矩教會人的核心不是別的,就是害怕,無論不滿足的NJ、覺得每日重複空虛的NJ公務員老婆、還是順風向做投機生意的NJ朋友,信守的本質並不是成功,而是被成功所餵養的害怕。
他們的世界裡,所有的階級始終如此分明,強調女兒的鋼琴獎狀、婷婷的綠色校服、老師的頭銜、人人掛老闆的位置,婷婷的名校閨女身影,對外界是充滿試探的,除了課業外,她其餘時是漫不經心的,這閨女只無暇他顧地專心做著外界的想像。
只有洋洋還沒有進入那個集體做著美國夢的「時空」,無法追尋一致化的光榮,拿著相機拍別人後腦杓、在學校幾乎沒有朋友、在家裡也很難插得上話的小男生,他其實是孤單的孩子,因此學會了另一種對話方式,拍出身邊人的背影,意外拍出了這世人夢遊的氣氛,我在哪裡?真的想要去哪裡?每個背影都是個問號。
 他其實是孤單的孩子,因此學會了另一種對話方式
他其實是孤單的孩子,因此學會了另一種對話方式
《一一》像是台北的一場夢,浸泡在前朝的夢,諷刺地殘餘民國的大國習氣,自己與故鄉的志趣與意識都不明,想跟著美國榮光亦不可得,即便是社區裡出現幾位建中、北一女制服的身影,如今連帶教育的摧枯拉朽也失去了風采,《一一》告別了我們自以為曾有的階級,自命的小布爾喬亞,那一代亦是被迫活在一個巨大問號中。
「婆婆,世界為何不像我們想的那樣?閉上眼,這世界好像才會美麗些。」婷婷夢中對奶奶說。
她父親NJ跟失去意識的丈母娘傾訴,「自己每天睜開眼總逼著自己要抱點希望,但失落總周而復始。」
與NJ談生意的大田則說:「你們既然每天起床都是一個新的開始,為什麼要害怕改變?」
 每天睜開眼總逼著自己要抱點希望,但失落總周而復始。
每天睜開眼總逼著自己要抱點希望,但失落總周而復始。
這部電影的夢境感像床被子蓋下來,一開始隨著陷入深深沉睡的老奶奶,讓其他人的將夢未夢,顯得如此掙扎,人人好像嘴裡還有餌的魚,從深海被釣出來般劇烈跳動著,幾個過了半生的中年人,為自己近在眼前的種種慾望而慌張不已,其實都遠得不能想像,或許真應了沃爾夫在《落失男孩》裡所寫的:「……事情的發展完全偏離我們當初設想的樣子,變得好像從未發生過……好像那些只存在我們夢境裡……接下來我們才會憶起事情的全貌。」
沒有一代知道我們其實被關進什麼「密室」?有著什麼樣的集體迷思?直到時不我予時,從遠古街角的風才會竄出來提醒我們,我們其實又重複了哪一代的人的錯。而如今已看來殘舊的台北呢?《一一》像楊德昌這般畸人的回眸,賭著正值壯年的我們與這城市重生的機會。
 《一一》
《一一》
《一一》為台灣導演楊德昌的代表作之一,是一部描寫家庭親情及生命意義的電影作品。楊德昌也因本片獲得坎城影展最佳導演獎的殊榮。2016年,獲英國廣播公司評選為「21世紀最偉大的100部電影」第8位。本片雖是2000年的電影,但因楊德昌對當時台灣電影的發行生態遭少數人把持的情況深感不滿,擔心會被草草上檔就此被犧牲掉,於是乾脆不上映,近期才有機會在台灣放映。故事劇情描寫台北一家人的感情起落及生活故事,探討人生在不同階段將會面臨到的困惑與危機,表達出對人的關懷與尊重。整個舞臺環繞台北為場景,看似平凡無奇的都市生活,感受周遭的人情際遇及生老病死,隱喻大家如何看待生命的意義究竟為何。
延伸閱讀 楊德昌的真實與獨立──王昀燕《再見楊德昌:台灣電影人訪談紀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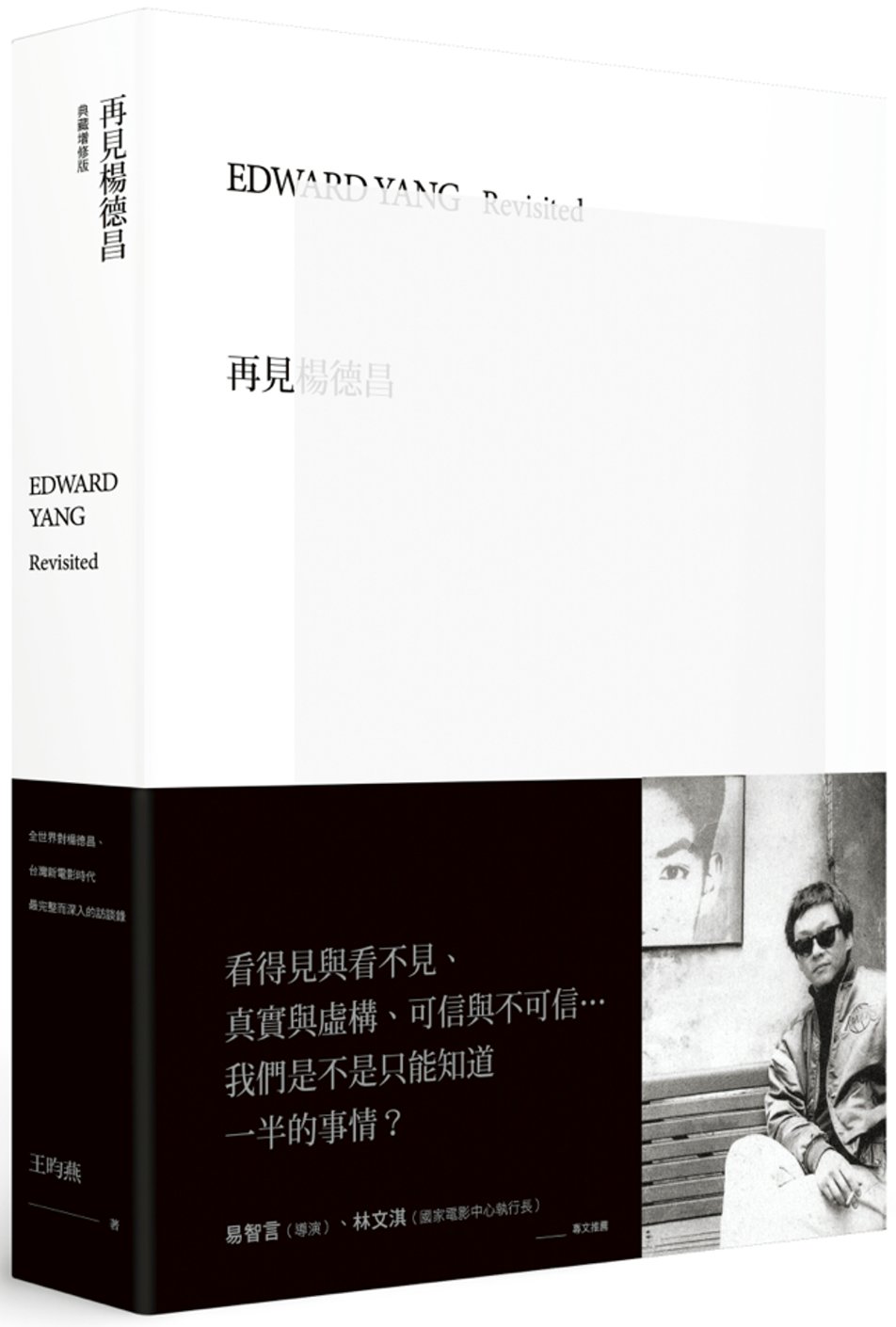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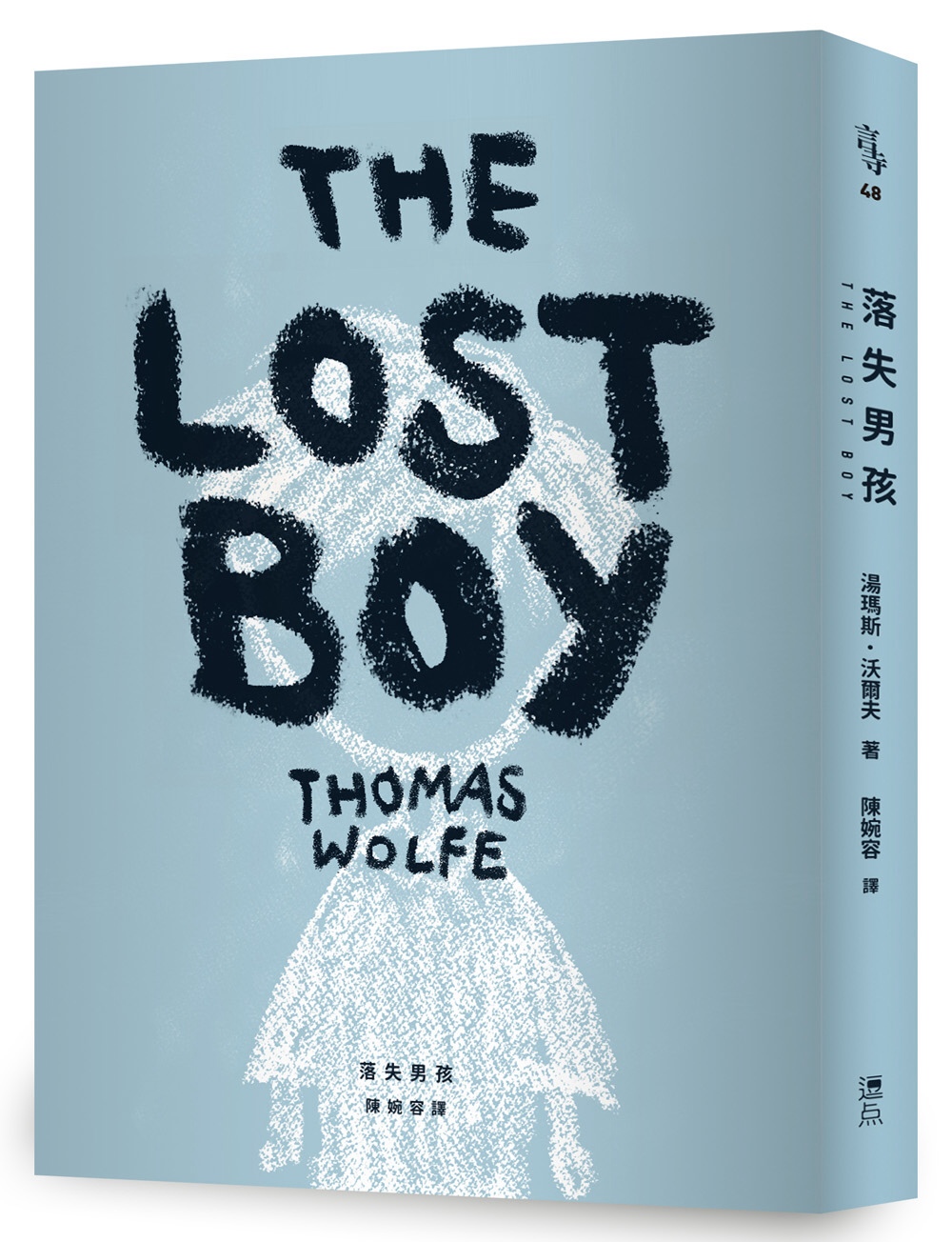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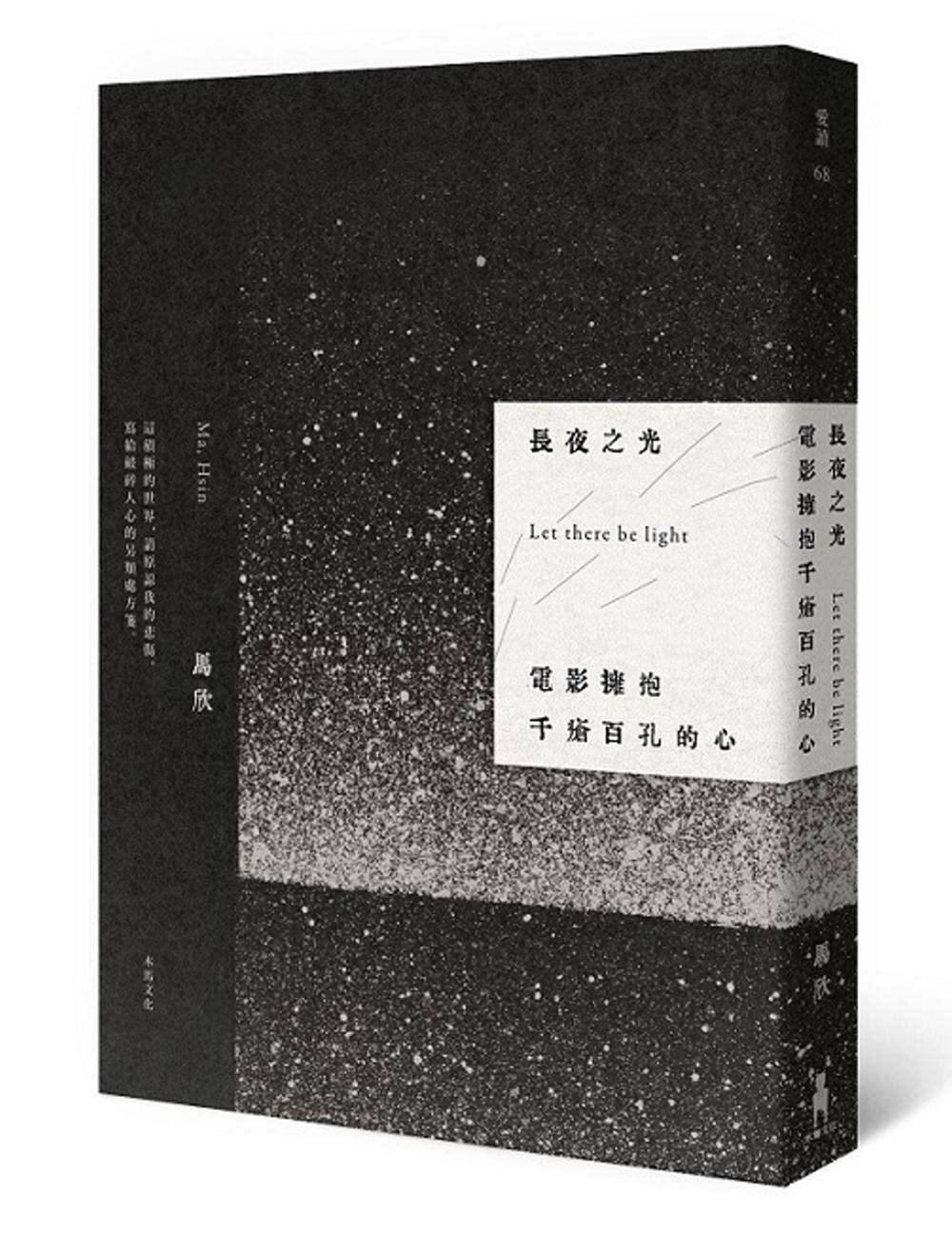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