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她」原是冷僻字,由劉半農在1917年首先提出,以因應翻譯西方文學作品時,面對「she」這個女性第三人稱代詞的尷尬。周作人接著於1918年8月5日出版的《新青年》,為文提到了劉半農這個建議,但引起保守者的反對。劉半農後來在1920年正式寫過一篇〈她字問題〉回應爭議(且乾脆一併提出了「它」字的用法),之後並用一首〈教我如何不想她〉,開始推行了「她」字。(其實在白話文運動初期,也有人用「伊」來指稱女的第三人稱——例如魯迅就是如此——顯然還是不如「她」受到了人們的廣泛使用。)
以上好像太複雜了。總之,強調與尊重女性是此時代的趨勢,據說「她」還曾被票選為二十世紀最重要的一個字,這一切都是無庸置疑的。然而,在文學的世界裡,不能總是完全仰賴政治正確。至少幾千年來的文化氛圍,諸多先輩都用「他」來共指男女第三人稱以及其他物體(雖說他們也沒有別的選擇),然而文學發展的高度並未因此受阻。何況迄今於日常會話當中,我們仍沒有像是英文發音那樣刻意分辨出「她」與「他」,也不至於引起什麼暴動,可見是否言必分出第三人稱性別,此事仍有迴寰餘地。(當然像李煒那本全篇動用第三人稱的角度以疏遠自身傷痛,才能順利哀悼他母親曹又方的《4444》(爾雅,2010),「他」與「她」的對比使用在結構形式上有其必要性。何況,此書是先用英文寫好,才被翻譯成中文的,因此也只能斬釘截鐵地標明第三人稱性別。)
若不論在什麼情況下皆無限上綱,非區分出「他」與「她」來不可,我們的損失是什麼?文學不免仍有不需要(或刻意不想)指涉性別的時候;此層蘊藉,此種詩意,原本是西方文學所未有,而幾千年華文所特有的,將近百年來,這種福利,逐漸被莫名地取消了。
在充滿想像力的文學國度裡,性別是可能超越僵化的現實,允許變幻莫測的。我們在百年前需要「她」來幫助我們強化出女性的地位,現在未嘗不需要維護一個可以兼容並蓄各種性別、物種、無生命客體的超然之「他」(在我們發明出另外一個更適當的字之前),來收容各種性別流動的美學可能。換句話說,「她」一定是女的,但「他」未必不可以是;「他」或許是男的,也可能是其他我們所無法預料的。
譬如當我提到母親,接著說「他」怎樣怎樣時,即使沒有使用到「她」,難道讀者會因此誤會我母親的性別嗎?所以我始終反對有些編輯想把我的「他」,積極全部改成「她」的企圖。
據傳劉半農當時還曾經賦予「她」字更廣泛的意義,除了性別之外,「自己格外珍視的事物」也可稱「她」。他在給周作人寫的一封信中寫道:「說起文學,我真萬分的對她不起,她原是我的心肝寶貝!」這種非關性別的用法,我們現在也不留存了。
此文固然是因為老是有人要糾正我的「他」是一個不合時宜之錯字所發的牢騷。更是希望,我們不會有朝一日,「進化」到一個非得分辨出「我」與「娥」,否則無法寫作的世界。也祝福未來的「她」,能日新月異突變出別的意義,超越身為女性代名詞的永恆宿命。
鯨向海
精神科醫師,著有詩集《通緝犯》《精神病院》《大雄》,散文集《沿海岸線徵友》《銀河系焊接工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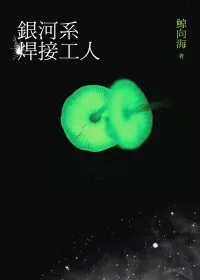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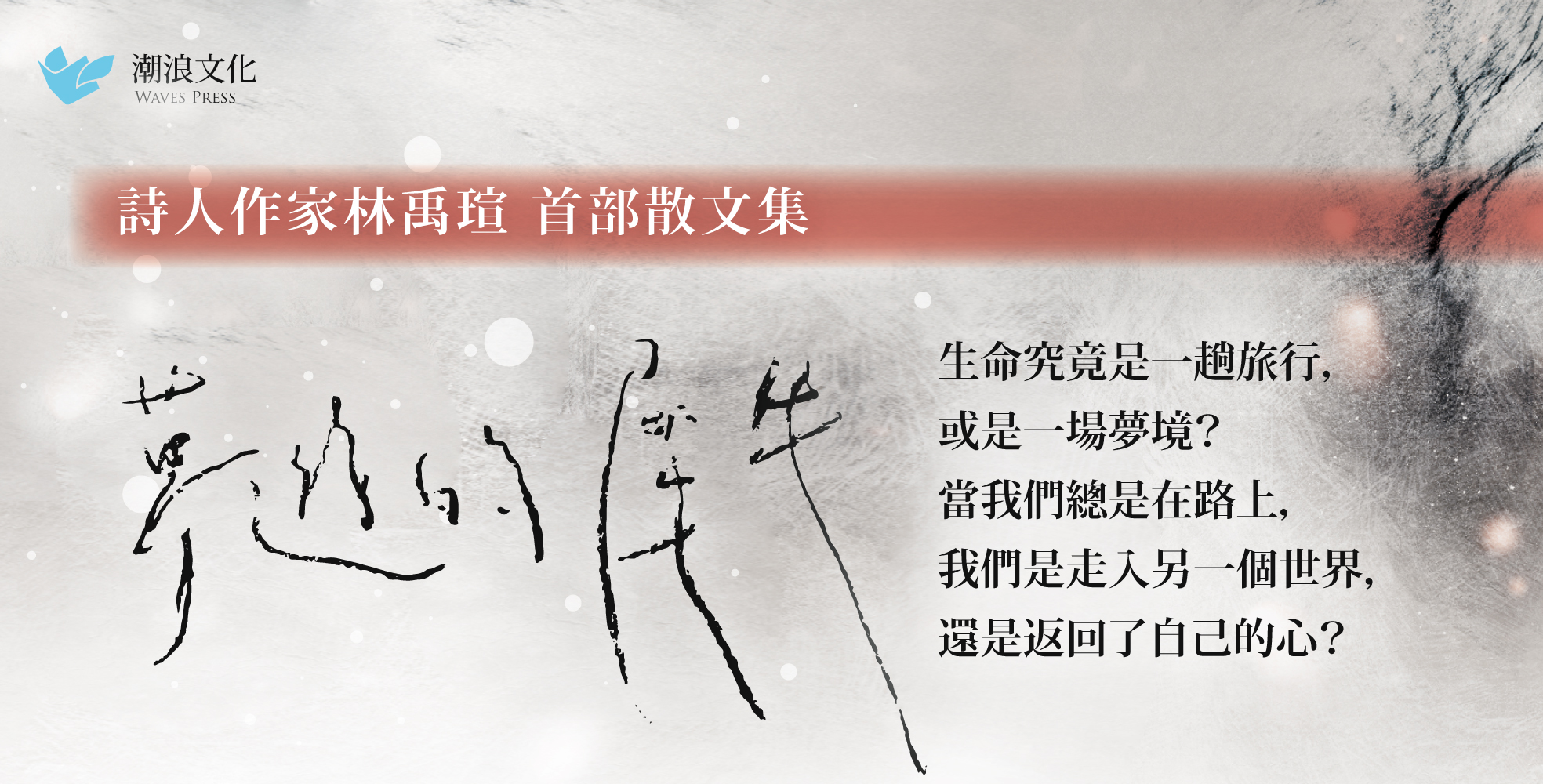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