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童年就像蒼蠅一樣揮之不去,可是討厭中又帶點美味之處,才一直招惹它來叮我。」文壇新手何景窗以古靈精怪且嘲諷大人世界的童趣口吻,講述自己童年的各種焦慮,發表了散文集《想回家的病》。為什麼想回家是一種病?曾獲梁實秋文學獎的她說,書名是取自英文nostalgia與homesick(鄉愁、想家),為了更平易近人,便直白地翻成中文。
1976年生的何景窗,從小就對「家庭」充滿渴望與困惑,她的童年,有離散也有寂寞,「我的性別不被原生家庭所期待,也很幸運地有了被領養的機會,」當時,領養家庭的媽媽在菜市場擺水果攤,爸爸則是退伍軍人,兼幫媽媽賣水果,姊姊哥哥分別大她13歲和9歲,白天也都上學去了,從小她就羨慕大家可以名正言順出門去忙。
家裡多的是裝水果的紙箱。它們有的拆扁疊在一起,有的像口井,飄出寂寞,果蠅像禿鷹一樣在上面盤旋。……只要他們不賣水果,我們全家就可以下班後一起晚餐,一起上床睡覺,週末一起看電視,像電視裡幸福家庭生活的那樣。——〈非中產階級兒童的家庭生活〉,《想回家的病》
在高雄左營眷村長大的她說,從小爸爸就叫她去加工區做女工,「小時候對職業因為沒有想像,所以沒有選項,」生活周遭的人普遍從事軍公教、加工區、小攤販或跟廟有關的事;為實現當上班族的願望,身為專業的電視兒童,天天看的電視廣告引起了她的興趣,於是便開始找資料,朝這條路前進,高職、二專唸廣告設計,文字則是她從小的專長,北上後的第一份工作就是進廣告公司寫文案,1999年還曾以「飲冰室茶集:雨後胡同篇」獲得時報廣告獎。何景窗說,「我是上了台北才意識到社會階層的差距,我想藉由書寫,回頭反思自己經歷過的資本流動狀態。」
何景窗的創作題材多圍繞著「家庭」,十年前她離開廣告圈,考上南藝大音管所,曾經拍過讓家人有點傷腦筋的家庭紀錄片《家庭實驗》。她說,那時迷惑於哥哥姊姊都邁入下一個人生階段,自己卻始終在家等他們回來,唯一有重逢的感覺,卻是兩次的父母辭世,「當時我內心受到很大的衝擊,真的不會再有人回來了,也逼著我們承認已經各自成家了,」如今想起,她有些羞怯地說,「我那時比較憤世嫉俗,腦筋迴路一直轉不過來。我一度很害怕自己,好像一直在傷別人的心。」
媽媽只和哥哥一國,他們兩人之國不需要姊姊和我。我可以感覺到我身體裡濃滾滾的醋酸和鹹切切的眼淚正烹煮著一顆心。——〈令人討厭的母子關係〉,《想回家的病》
何景窗說,哥哥從小就功課好長得帥,跟媽媽感情特別好,自己永遠在他們的關係之外,常常是姊姊照顧她,像個溫柔的媽媽二號。
她在書中也傳達出對於性別不平等的反彈,「對於被領養,我其實很開心可以擁有兩份家人,只是這個社會體制為何會造成這種現象,是可以思考的,」於此,她有話想講,那也是促使她大量閱讀、認識社會的原動力。
四年前,她陪女友到倫敦唸書,《想回家的病》則是這段期間她在《中華日報》副刊的專欄集結。去年哥哥到比利時開會時,曾繞到倫敦找她,兩人就在希斯洛機場長談了六小時,緊繃多年的兄妹關係因此冰釋,「從沒想過我的同志身分,能得到家人的接納,」因為他們擔心這麼多,才阻止這麼多,何景窗說,「我不會把當時對立的力量視為迫害,反而是當你心念改變時,可以重新開始的起點,」包括她主持女同志廣播節目《拉子三缺一》時,想的也是如何讓同性關係能併置於傳統家庭的架構之下。
「由於寫的是童年生活最親近的人,筆觸尤其需要斟酌,」她說,記憶是單向性且難以考據的,寫作時就好像在做化學實驗,要分析一個情緒,得不斷調到溫和的中間值,「我很怕自憐的同時,會傷害到家人。」
《想回家的病》出版後,何景窗最希望小孩子也可以看得懂,尤其是喜歡《小淘氣尼古拉》的那群小孩,因為這就是一本女生版的對照組。那麼,這個病痊癒了嗎?她童趣地笑說,「我因為知道別人也有這種病,所以好過多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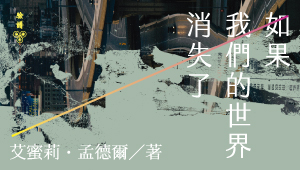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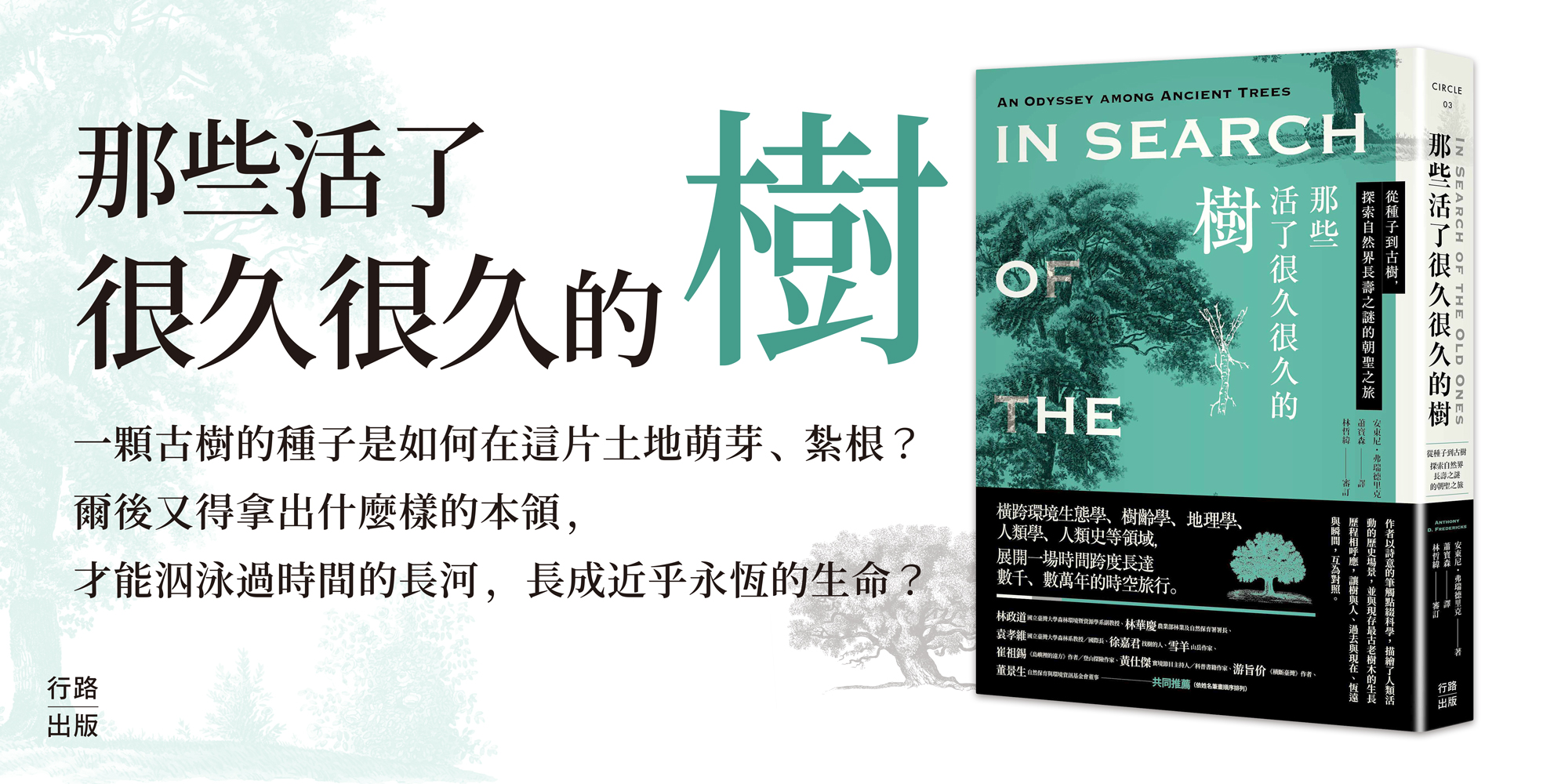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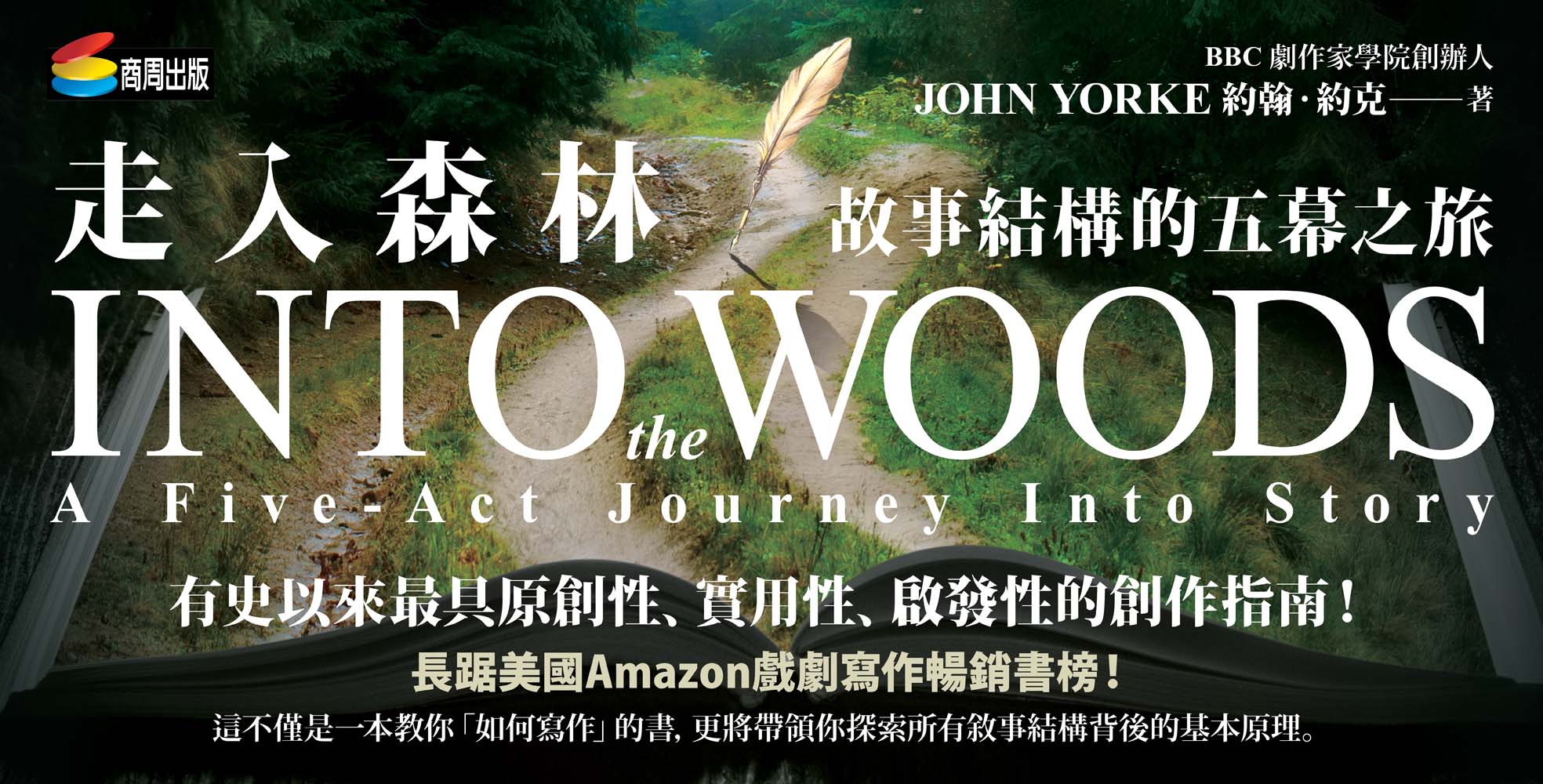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