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父母都是客家人,但自小搬離苗栗、加以幼年國語教育之強勢,我與兄弟雖有客語耳朵卻無舌頭。從前沒發現語言在我身體的哪裡種著,只記得有一回學校放交工樂隊的紀錄片,猛然聽見那滿山滿谷嗯啊曲折的客家日常對話,像中邪一樣淚流滿臉。
從父親家走田埂捷徑大約七八分鐘可抵達母親家,母親跟我說過兩人初相識的畫面,說奶奶與外婆講起,家中未嫁娶兩人說不定很相配:「不如你家明堂改日來看看吧。」外婆應道。
長子我父親沒什麼心機,聽了奶奶的話也就乖乖去探路。「遠遠看見一個小伙子牽著頭牛,咧嘴笑著走過來啊。」母親說得眼都彎了。
爺爺的房子是自己設計監工蓋出來的,我在整理老照片時看見許多房子剛落成時所拍的各式角度照,心裡想那時他不知有多得意。我喜歡他前幾年時常還很有精神遞給我看他的日記,那裡頭寫的不是平常心情,而是他每日閱讀國際時事的摘要與心得,關於太空電梯或農業技術改良之類的,全是日語夾雜少許中文。臨出國前他對我說:「我們家有流浪的血,到這代還是。」從他口中吐出「流浪」這個詞,違和中帶有些許傷感。我知道他說的不僅是我,更多是他半生思念的遠方親人。

我所認識的客家人,絕大多數台語都說得十分流利,那是生存必須使然。這種為生存而扭曲或衍生的技能,幾乎是無需心理掙扎便自然長成的,我記得幼時學校有一陣子推行說唱藝術,口齒清晰不怕生的小朋友為了參加比賽或表演,每天中午得犧牲午睡時間,練習舞台走位與打竹板、強記相聲段子裡不見得能消化的包袱。不過小學五六年級的我,雖然對於時有公假可四處遊歷感覺新奇,也樂於接收師長的稱讚和偏愛,但已經隱隱察覺過分強調的捲舌音在小學同儕當中的格格不入。出於一種自我保護的本能,在離開大人和同齡孩子相處時我會特意用台灣國語說話,有沒有收到交友順利的效果至今還是看不清,但當時小心翼翼調整腔調、深怕被排擠的心情仍難忘懷。
我的國中地理老師姓丁,每回上課前會讓同學先在黑板上畫好中國某一省份的地圖,再標上河川山林鐵路與省會大城,上課時點名抽考,指認有誤的女孩打手心,男孩則趴成一座山打屁股。我國中剛畢業已對那岸的水文礦產印象全滅,更慘的是大學聯考時連野柳究竟在台灣島哪一頭都搞不清楚,儘管大一修詩選讀到阮籍日暮途窮而哭會與教授淚眼相望,但在那之前完全沒有聽過賴和的名字。面對疆界以及歷史,無論是在知識或者常識的領域,我兩頭皆空。
這實在是沒有辦法的事,相較起國族及文化認同,性別才是我第一條被磨銳的神經,它既強大又將感官充滿使我驕傲苦痛,幾乎沒有任何餘裕能夠在意他事。我先成為了女性、誓死愛慕女性,許久之後再成為了一名台灣人,此後重學作台灣人。
四月初飛離台灣進行兩個月的駐村,是時立院學生尚未出關,台灣幾乎沸騰。仿佛要為無知無覺的前半生懺悔那樣,行前我到地方圖書館借了二二八口述資料與白色恐怖史料,塞滿半個行李箱,打算閉關自習。飛過七海七洋,我仍徹夜占據網路頻寬關注新聞實況,與人相交,張嘴無法不提及「我們台灣」現正經歷之事,多麼像戀愛,一點也藏不住。夜裡餐食用盡,酒後的話題開始顯得雜沓且沉重,在我勉力為整桌人惡補台灣近代史之後,西班牙攝影師接著談起內戰時至今日還如何沉默分裂西班牙人的心,我領悟人類的歷史並無新鮮事,唯有各人慘烈與忍耐的活值得流傳。
《嘉義驛前二二八》盧鈵欽醫師妻子林秀媚的訪談稿裡,這樣描述一九四七年那厄運降臨的一日:「他們被槍殺的那天中午,聽說全嘉義的午飯沒有人吃,都剩下來,都很驚訝這個社會怎麼變成這樣。」(頁224)林秀媚女士用詞直接而生動,同情共感之際,你會好奇人的記憶與感情如何收藏、投射,而後為他心再現。那使我近來在閱讀《無法送達的遺書:記那些在恐怖年代失落的人》時,除卻直抒情懷的惆悵之外,面對不同創作者為人物事件所進行風格各異的詮釋,不得不抽離情感鄭重看待:正直不一定會抵達真理,謊言有可能暴露實相,在悉心愛惜的老相片以及重見天日的絕筆字跡之間,點醒胸中星火、遍燃愛苗之後,我們的詮釋是否頂得住時間?被再記憶的記憶顯然重生,重生後的面目是否可能不再為時代服務,是否能為九死一生的記憶指引一條蹊徑活路?
此問萬分艱難,是所有願望記得、與我同樣半路重學作人的人還得面臨的焦慮與辯證。記得從來不易,記得我們所身處的此時此地並非偶然、亦非憑空而得,記得人與自己的土地、與先祖之間,遙遙呼應並近身實現的情感。記得人的惡與苟且,記得無名天使。記得自己所遺忘的,不為所囿,而後得以懷持一個更大的文化圖像。
春天在法國鄉下讀到的訪談中,林秀媚女士說了一句話,鬼那樣跟著我,一直在眼前重演,我最後無計可施,寫了篇萬字小說,只為把這句話寫進去。小說寫得太急,沒寫好,現在重看仍非常言情非常微小,還沒對得住那隻鬼。我時常想,無論寫過幾次、如何書寫,有一天我們生者都準備好了,死者便能安息嗎?又或者沒有準備好的時候。他們為我們而死,我們沒有理由可以平靜度日。所謂記得,也許便是自覺不願平靜,眼見百鬼人間遊歷。
羅浥薇薇
八○年代出生。台灣苗栗人、左營長大。
現職為幼兒電視轉播與保育員、不自由創作者,未來不詳。 著有小說《騎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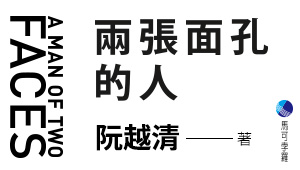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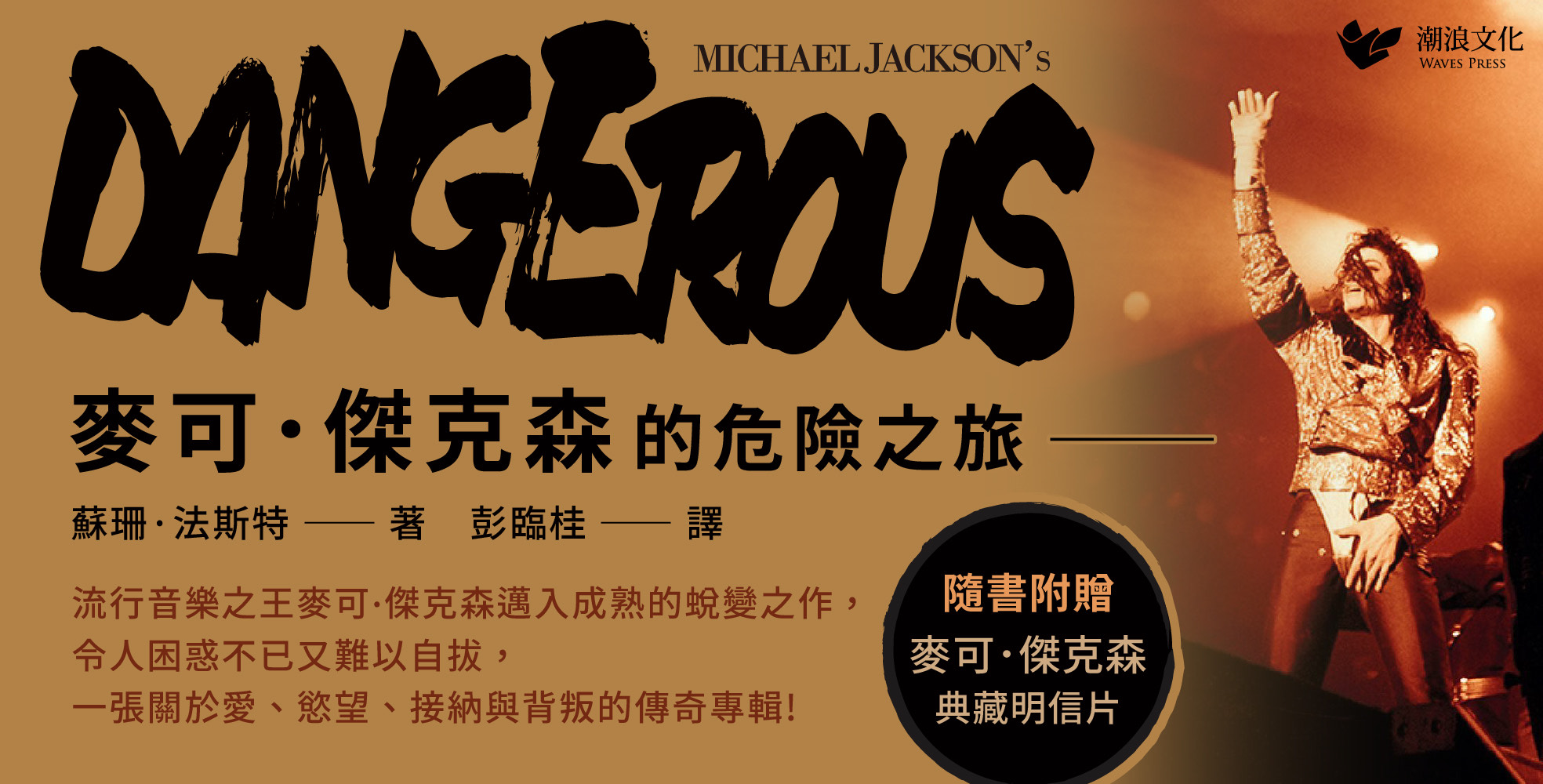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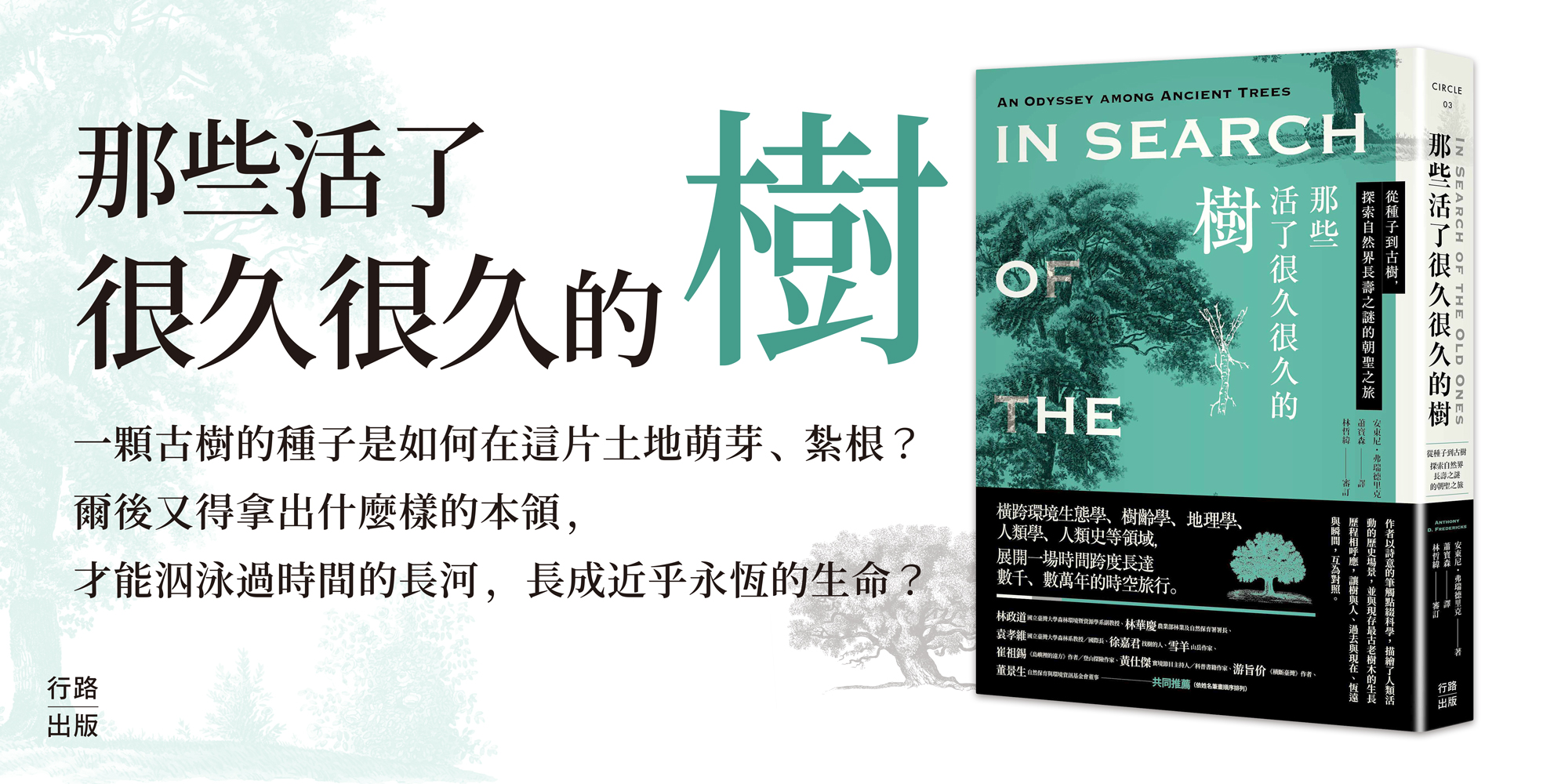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