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漂浪的移工們,帶著受傷的身體,捧著受苦的心靈,一路拚搏跌撞終於返鄉,然而,《回家》竟不是一個歸鄉安身的故事。回家之後,路還長,且更顛簸艱險。
曾經以「我在場」為寫作方法,老實記下菲律賓移工故事的顧玉玲,這次將鏡頭移至越南,轉換視框與角色,從戰鬥者到異鄉人,眼界更為開闊,故事卻更難述說。
2008 年,《我們》出版後,顧玉玲便起心動念書寫跨國移工們「後來的故事」──他們離開台灣後到哪去了?返鄉後的人生過得如何?2009 年,顧玉玲前往越南調查仲介制度,短短兩個月間,她拚命看、奮力記,留下十萬多字田野資料。回台後,又陷入移工運動每日的烽火戰事中,書寫不得不暫時擱置。直到離開組織,卸下工作崗位,這些文字才又重見天日。2013 年,顧玉玲再次前往越南,見了人,辦了事,返回後動筆,至此累積了30幾萬字的素材需要她築牆蓋樓,重新裁剪組裝。
《我們》是現在進行式,運動一邊走,文字一併落下,寫作時間停格在 2007 年底,書也付梓出版。相較之下,《回家》處理的時間跨度長達15年,人物多,事件雜,剪接的鑿痕斑斑,顧玉玲坦言:「我不斷打散重編,一開始整理時,五個章節的結構就出來了,再來則是慢慢拼貼人物的交錯、遭逢。我到了送印前一週還在改,戰戰兢兢,忐忑不安,一直很怕自己有誤解。畢竟他鄉異地,我這回成了異鄉人,總會擔心自己的功課做得不夠,更害怕因為兩地的發展速度不同,下筆時會帶著自以為是的傲慢和偏見。」相對於《我們》的快刀俐落,《回家》的字裡行間的確洩漏了她異鄉人的身世,全書充滿人類學式的細節,一屋一瓦、各類吃食,處處不放。「我其實已經刪掉很多了啊,所有與台灣不同的東西我都會忍不住寫下來。但其實也讀了大量的歷史和越戰小說,同時思考如何放進歷史的厚度。」
越南不只是美麗的下龍灣。只見顧玉玲乘著摩托車在城鄉間穿梭,從這村到那鄉,也帶著讀者重新認識這個國家。不過,顧玉玲接觸過的移工來自東南亞各國,為什麼選擇越南?「我對這個社會主義國家如何快速地資本主義化一直感到好奇。」而同輩越南女性的父執輩在戰爭中傷亡的故事也讓她著迷,「這和我們很不一樣,戰爭是她們兒時的記憶。不像台灣,我們被殖民,不曾親身經歷戰爭,如此不同的歷史對照對我而言非常有趣。」
除了戰後亞洲國家的歷史對映,年輕時代的反戰啟蒙也是關鍵。「我們這代人的進步意識啟蒙多是反戰,其實就是反越戰。當時我們對越戰的認識多來自好萊塢電影,我閱讀了很多越戰的歷史和越共的故事,對他們有很深的敬意。」顧玉玲在訪談時經常聽到老人家提及越戰時展現出的民族自尊心,那般自信的態度,在年輕一代的身上幾乎看不到了。改革開放後,他們揚棄舊的歷史努力向前,但歷史在他們身上烙下的矛盾和衝突卻難以迴避。

凝視異鄉,照見自己
相較於《我們》中有意識把持的戰鬥位置,帶入自身的家族故事,顧玉玲在《回家》則相對隱身,退居為紀錄者的角色,也讓《回家》成為一本「他者」之書。她自陳:「所以我也會擔心這本書對讀者來說是否相對有距離。我讓自己放入《我們》是一個經過清楚判斷的政治立場──我一定要說出我是誰。但在《回家》比較是衡量我這個異鄉人要看到什麼程度。其實,當我進入這個他鄉異地,難免還是帶著自己的想法進場。眼前這個每年 GDP 成長8%的國家就好像七、八○年代的台灣,但我也知道這一切掠奪式的開發,終究會走向對平民百姓不利的狀況,但又面對到集體的欣欣向榮,當大家開始邁向現代化和進步的繁榮生活……這讓我有一種預知死亡紀事的感覺,但……又不能這麼理所當然下結論。所以,我經常掙扎於自己的意見到底要出現多少。最後,我讓自己退一點,讓眼前的東西出來一點。」
然而,就算從「我們」轉向「他們」,書寫者依舊得面對自己的位置該如何安放,如此書寫畢竟不只是報導或紀實,每一次傾吐的背後都帶著超越採訪關係的託付與信任。沉吟許久,顧玉玲緩緩地說,「影響我的其實還有一點,組織的分崩離析讓我的戰鬥位置並不清晰。我還是把出書當作社會運動的一部分,可是,書寫時剛好面對到組織內部的分裂,以及我自己在運動中的迷網,這讓『我』的角色再退一步。但我也曾想過,如果不是這樣的話,我的角色會有什麼不一樣嗎?好像也未必。我的角色在《我們》裡面已經清楚了,似乎也不需要再回頭一次。」
返鄉路同樣迢迢,生命卻各有機遇和選擇。有人陷落,就有人拔高。《回家》裡的人們際遇殊異,顧玉玲下筆時儘管保持中立,仍不免透漏了她的喜好與評價。「這裡頭當然很多人選擇的生活方式和我做為一個社會運動者不是那麼相合。我也許不是那麼同意,但那可能是她們在有限的條件下,最好的選擇。不過,也許同樣是往上攀爬的人,我對她們其實有情感上不同的評價,當她們揚棄過去的身分,轉身去過更好的生活,許多不好的紀錄是她們要丟棄的,但我也不忍苛責,條件有限,誰不會先墊高自己呢?」
面對不堪的人性,工作者的身分讓她無所遁逃,如此近身逼視,毫無旋身的空間,不禁好奇顧玉玲究竟如何下筆?「書寫者的特權就是在既有的情節,給這些人一個安置的方式。」於是,阿蓮的故事收束在她於田中勞動的場景,「我覺得那是她最充滿生命力,也最療癒的片段。她的恐懼其實沒有藥醫,但當我看到她在田裡的樣子,就放心了,土地與農務的勞作會讓她被治癒。她們知道我要寫,也好慷慨。我覺得女人在揭露自己的傷痛挫敗的時候,比男人都勇敢太多。那麼,不辜負她們的方式就是如實呈現她們錯亂、痛苦、畸零的生命狀態,我希望有寫出她們很強壯的生命狀態。」
顧玉玲投身移工運動十數年,交出《我們》《回家》二書,也為台灣文壇留下難以歸類和評價的珍貴文字。如此與人近身交關、與政府衝撞的厚實經歷,也難有虛構作品得以企及。訪談最後,不免老套問了下一本書在哪,顧玉玲難得鬆懈喊累,「還沒想到下一本書。倒是會惦記以前在工傷協會累積的資料……但想到又……好累。這是一種責任感,我在社會運動裡累積了很多、貼身經驗了很多人的生命,這些都是滋養我的養分,這些滋養應該要成為公共財,從我的經驗裡轉化出來。不寫下來的話,會不甘心。不寫,就沒有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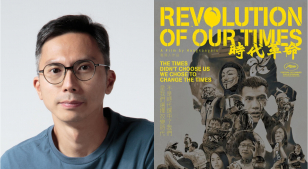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