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攝影/但以理)
一束長髮,大眼雪亮,說起話來和緩溫慢,一字一字,單顆單顆地,如珠玉般吐出。
當網路上匿名「運詩人」的房慧真坐在眼前時,很難想像,這名看來秀雅柔婉、富含文氣的女子,筆下所書寫的俗常見聞樣貌是如此冷銳,如一把劃入城市底層的手術刀。一如房慧真身邊的朋友也都很難想像,害羞內向近乎自閉的她,竟然會有任職媒體的一天,還是日日與人頻繁往來的記者。
從《單向街》到《小塵埃》兩部散文集,五年的時間,房慧真歷經了生活與身分上的轉變。2011年,她結束了長時間的學生生涯,正式踏入職場(且是堪稱最激烈最腥血的媒體),跌破一堆原以為她會在學術圈內安身立命的眼鏡。因著工作,她開始走出原本封閉穩定的自我宇宙,對世界伸去收送的觸角;延伸到她的書寫上,她說,她似乎慢慢從一個讀書人,試著轉為一個創作者。
「當學生好像是一種豁免,可以讓我有很多時間去做自己的事,讀自己想讀的書,看自己想看的電影。以前過得其實是一種有點任性的、某種文青的生活。」房慧真家住台北、生活簡樸,相較起他人,少了租屋壓力與琳瑯物欲,經濟上稍有喘息空間,「平常接些稿子、兼個家教,生活就也還過得去。」2007年的《單向街》,就這樣在豁免之下累積而成,很純粹,很個人,或者如她自己所說的,很「掉書袋」,總在每一篇文章裡,認真地填入許多閱讀後的反芻。及至此回的《小塵埃》,純粹依舊,個人依舊,多的是她在工作之後,用同一雙眼睛所得的、更交錯複雜的世界,以及她希望自己能夠培養出的,更強大的直觀。
「我以前比較活在自己的世界,也非常懼怕與陌生人攀談,對任何人事物的觀察,都保持一個距離。」彼時的房慧真,也就像是一條單向街,直線前行,只進不退,幾乎不與他人交錯。喜歡走路的她,總以這樣的形式,看望著路上的一切,或貓狗,或人家的陽台,或冷清的攤販,或坐臥路邊的流浪漢。緣此寫下的景物,清晰明朗,像是隔著一層透明玻璃。當她成了一名記者,彷彿取得了一件能幫她近身觸碰的防護衣,甚或一個神奇的切換開關,讓過去怯於開口的她,能夠自然地突破藩籬,朝這些對象發出探問與好奇,看進那些更深入的,與未曾想像過的。
「我從沒想過自己有一天會去採訪這些以前觀望著的遊民或弱勢者。而一旦眼前的觀察者變成受訪者,寫作者跟寫作題材之間的距離,也就發生了變動。」於是她寫起了這些底層人們的故事,流浪漢、殘疾人、拾荒者;因著工作,她也寫起了光鮮亮麗的名流,或短暫的一瞬,或長些的片段。她與這些對象或多或少都發生了過往缺乏的交流與互動,但不論是她,或是這些人事物,都不是那麼緊密黏著,轉眼便會飄走,是她所謂的小塵埃。
而在書寫這些小塵埃時,房慧真希望自己可以用一種更敏銳、甚至是更野獸般的直觀來描繪,「我是個一不小心就會過分認真的人,常常為了寫一篇文章,讀上二十本書,或看上十部電影,把自己弄得精疲力盡,不管是部落格或工作上的文章都一樣。」所以她總在文章裡寫入許多從某些書或電影得來的延伸,「寫得太緊了。」她自己說,說是物極必反。「這幾年我就嘗試不要在文字裡提到任何一本書、任何一部電影,希望單純是眼睛看出去的、直觀的世界。」她並不是要一舉推翻自己長年閱讀所奠下的學院性格與基礎,只盼能撇下所有知識包袱,磨出無迂無迴的感官。

(攝影/但以理)
許多人稱房慧真的文字冷酷冷感,甚至過分犀利,特別是那些關乎生活的部分,不論是己身或他者,其直入的程度,往往令人不忍對視。「這可能是我比較自覺的部分:我是不是把自己的同情或憐憫,廉價地一次性就用完了?」於是她寧願用不帶任何情感與價值判斷的呈現,將自己的熱情熱性層層裹起,包入看似無動於衷的冷然眼光裡。
「我覺得再怎麼樣,最重要的都是看世界的那雙眼睛,為什麼有些事情你看得見、我看不見?接下來才是寫的風格、題材與筆觸。」房慧真以溫情的眼去看,卻以不帶溫情的筆去寫,如飛鴻雪泥一般,寫下小塵埃確實的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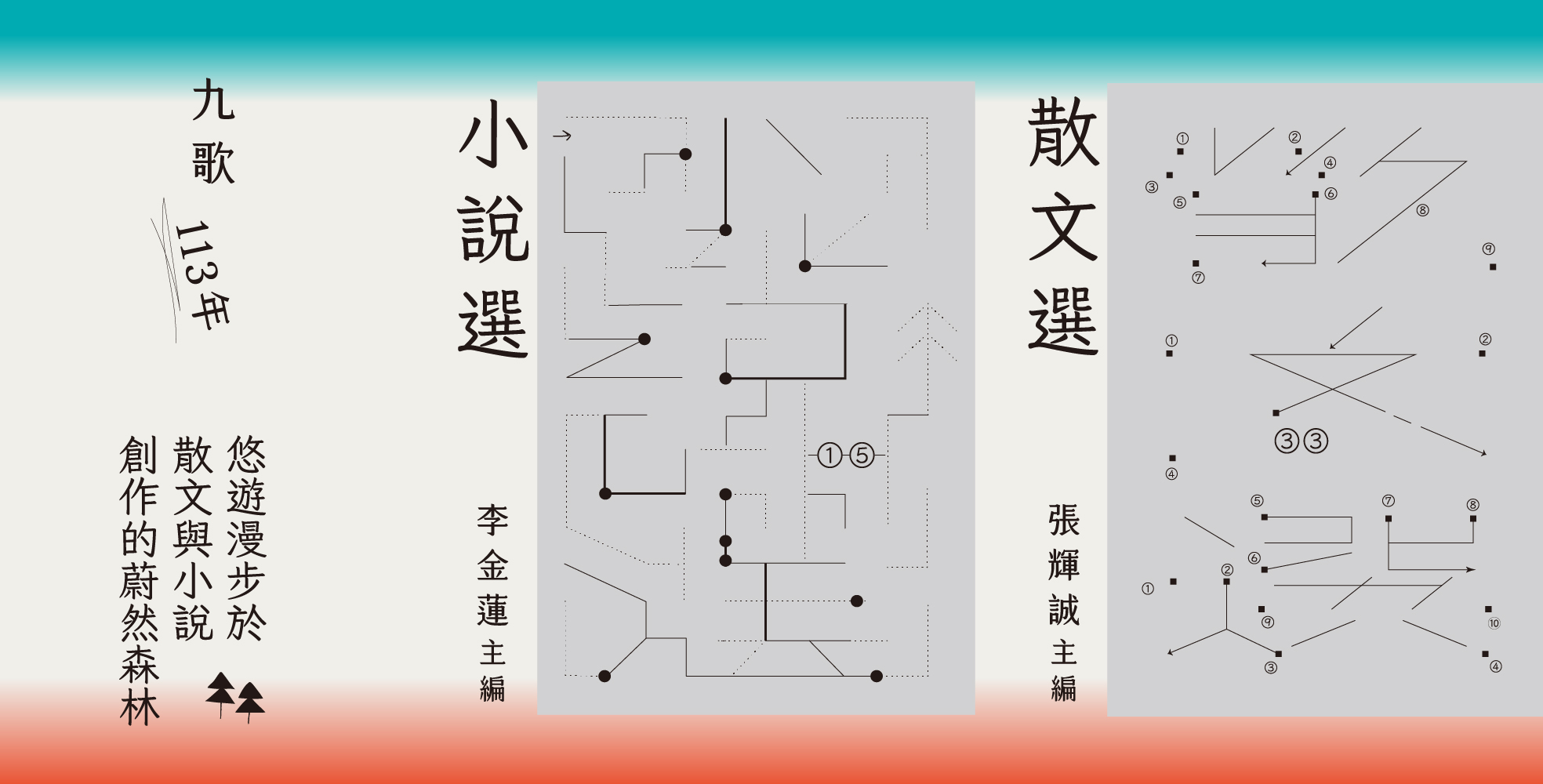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