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灣近來出現一個流行辭彙:「曖昧對象」。曖昧對象跟當事人之間或有情,或有慾,但還沒有定下來成為情侶。曖昧是浮動的,而不是固定下來的。這種浮動的狀態應該讓很多人沒有安全感,但太多人與人的情感就偏偏是曖昧的。不只對象是曖昧的,對象和當事人自己的關係也是曖昧的,就連當事人自己也不大瞭解自己要什麼/自己是甚麼。
「同志文學」和「文學中的同志」也是曖昧的。我並不願將同志文學的邊界畫得太死,也不願認定某些文學作品中的角色必然是(或不是)同志。畢竟文學尊尚曖昧,曖昧帶來想像空間,而被說死的文學/作品/人物則必定無味。
劉春城(1942-)的長篇小說《不結仔》(圓神,1987年初版)就是一個曖昧的例子。這本書大概不是同志文學作品,書中主人翁「不結仔」(按照上下文來看,應指「彆扭的人」)可能不是男同志,但這本書容易讓人聯想起青春期的男同志意淫。我覺得根本不用為此書人事物貼上同志的標籤,光是聯想和意淫就帶來不少曖昧的樂趣。
這本書描述鄉下男孩不結仔在青春期對於性的好奇心。在此書附錄的〈評論〉(現在的用語應為「推薦語」),龍應台寫道,「非常純樸的一本小說,在純樸中有一份忠實於鄉土的真實,一點都不做作,很好。」龍的推薦語會出現在這裡,可能因為她當時正是圓神出版社捧紅的作家──《不結仔》書末顯示,《野火集》已經賣了91版。另一方面,龍在1980年代也以文學評論著稱,她的《龍應台評小說》也曾經是暢銷書。龍當年也寫了《孽子》和馬森《夜遊》(書中男主角是雙性戀白人)的評論;但與其說龍特別留意男同志文學,不如說她走紅的時候正好是男同志文學及文化磨拳擦掌、蓄勢待發的年代。
龍淡定,說此書純樸;另一位書末推薦者卻淡定不得,以滅火的口吻說,「它(此書)不是一篇輕薄的色情故事……(它)藉著少年性事作文化倫理性的探討……」也就是說,這位推薦者並不覺得此書純樸,反而驚覺書中有少年的性,卻又連忙說少年的性不是色情,還說少年的性可以讓人認識文化與倫理。
這段承認性卻有否定色情的推薦文,載自傅百齡所寫的〈一個中國處男的故事──試探《不結仔》的中國性倫理〉。此文原載《新書月刊》(當年龍應台常在此刊發表書評),後收錄在《不結仔》書後。此文的主標題和副標題都強調了性與中國;事實上小說內看不到中國,但卻看得到性。此文很敏銳地整理出書中四大特色:一,不結仔很想有性經驗,但不敢上場;二,不結仔覺得自己的性器官比別的男生小因而自卑;三,不結仔「疑似同性戀」;四,不結仔似有戀母情結。
傅文指稱此書疑有同性戀,但又隨即澄清說書中其實沒有。或有人笑問傅既然不覺得書中有鬼,何必多次一舉繪聲繪影,其實根本完全不必疑猜書中有鬼。然而傅文的徒勞自問自答,卻展現了從當時一直到現在的某種詮釋焦慮:文本中好像有個「秘密的知識」(這個秘密往往是「性的秘密」,而此處性通常是禁忌的性,如1980年代的男同性戀),但詮釋者一方面無法證實這個秘密是否存在,另一方面又不吐不快、不願彆住不說心中有鬼。這種心態,其實是從古到今國內外驚悚小說的基本橋段:現場是不是真的有鬼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當事人心裡先有了鬼。
傅文對同性戀疑神疑鬼,顯示出1980年代當時的評論者已經知曉了同性戀的存在,甚至還自認為懂得辨認真假同性戀。這種新知識(「關於同性戀的知識」)的獲得與知識帶來的自信(「同性戀的真偽,我懂得分辨」),證明了1990年代之前的同性戀並不是讓人想不到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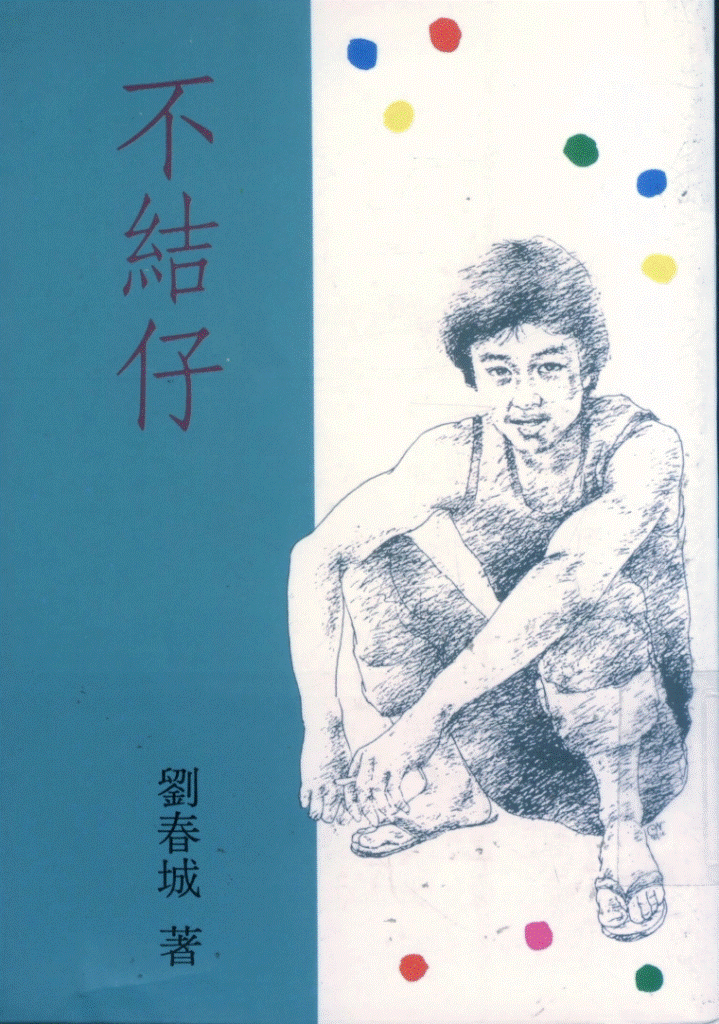
(圖/紀大偉提供)
雖然《不結仔》的敘事終究安排每個男孩都各自找了女人,但這個敘事與其說是在著墨男對女的幻想,還不如說是在琢磨男對男的心癢。
紀大偉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比較文學博士。作品曾獲聯合報文學獎中篇小說首獎與極短篇首獎等。著有短篇小說集《感官世界》、中短篇小說集《膜》,以及評論集《晚安巴比倫:網路世代的性慾、異議與政治閱讀》,編有文集《酷兒啟示錄:台灣QUEER論述讀本》、《酷兒狂歡節:台灣QUEER文學讀本》,並譯有小說《蜘蛛女之吻》、《分成兩半的子爵》、《樹上的男爵》、《不存在的騎士》、《蛛巢小徑》、《在荒島上遇見狄更斯》等多種。現為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專任助理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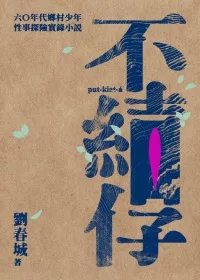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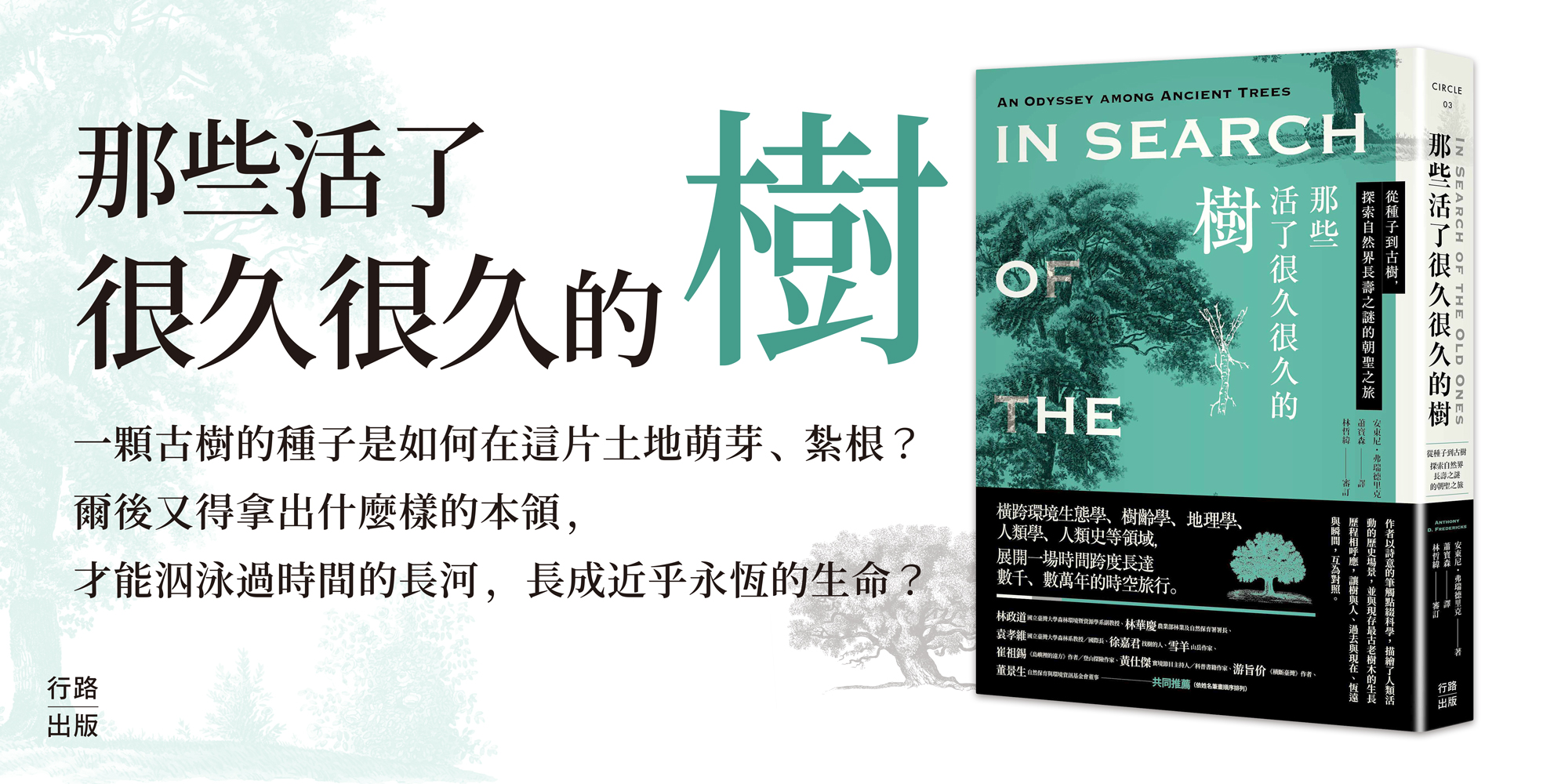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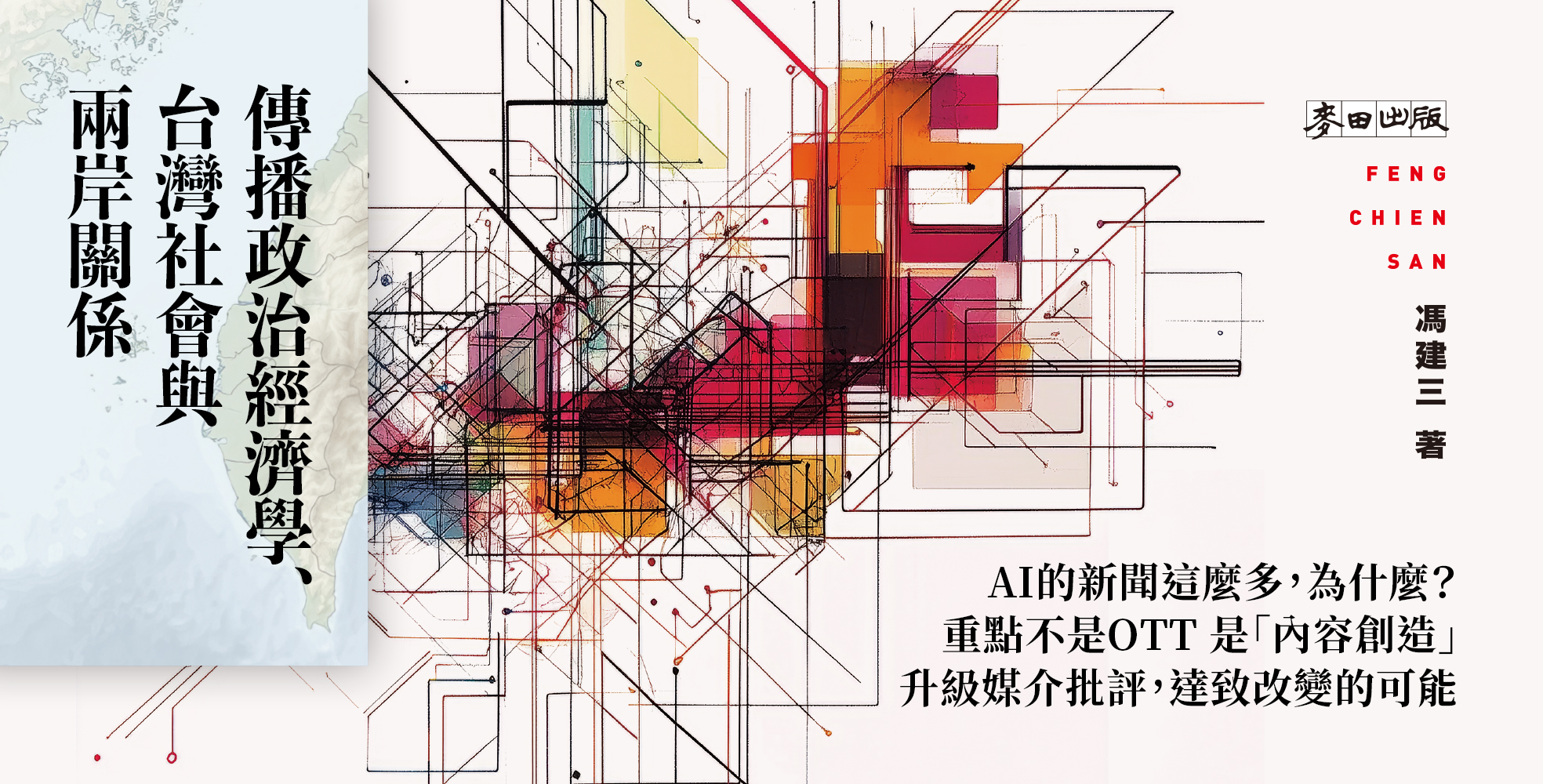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