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身在一間偌大華美、正深陷無可挽救的大火的白色旅館。火燒得如此之慢,人們仍可以任意進出。我看不見火,但煙霧濃重地瀰漫四處,尤其在燈光周圍。那真美。我既匆忙,又想拍照得不得了。我到我們的房間去拿必須營救的東西,不管那是什麼、我都找不到。我的祖母在附近,好像是隔壁房間。我不知道我在找什麼、我必須救什麼、這棟大樓還要多久會崩塌、我非得做什麼、我還可以拍多久。也許我根本沒有底片或者找不到我的相機。我一直無法專心。每個人都很忙、都在晃蕩,但一切既安靜又有些緩慢。電梯是金色的,像正在沉沒的鐵達尼號……我滿心喜悅卻同時焦慮困惑,遲遲無法進行拍攝。我的一生都在那裡。那是某種冷靜又痛苦地被封鎖的狂喜,就像妳的小孩即將臨盆,護士卻要妳忍著,因為他們還沒準備好。我幾乎要被那喜悅所征服、又被那其中的干擾所苦。天花板雕著愛神邱比特。倘若我試圖營救任何事物包括相機與我自己,或許就沒法為這一切攝像了。我感覺奇異地孤單,儘管人們圍繞四周。他們持續地消失。沒有人告訴我該做些什麼,但我擔憂著,唯恐我忽略了他們、或者什麼我該去做的事。就像慢動作播放的緊急事件,而我身在暴風之眼。
——黛安.阿布絲 〈一九五九年記事本裡的一則夢境〉(譯自《Diane Arbus Revelations》/ Random House, Westminster, 2003)
我到得早了,就先進藝廊,Diane Arbus 的原作比我想像中小很多,使人感覺不大真實。這是午休時間,齊歡趕著從辦公室過來與我會合,她輕輕從背後拍拍我,我們安靜地把展場走過一輪。
走出展場我們信步到附近的小公園,是難得的好天氣,草地上三三兩兩曬著人。齊歡說話的時候眼睛會很認真地看著對方,尤其是舉起酒杯要乾盡的時候。「要看進對方的眼睛才能真正傳達心意啊。」她會一次一次低下頭把我的眼神撈起,迫我記得這尚未在我心上紮根的文化習慣。
「看了這些照片,讓人好想放下一切橫越美洲大陸。」她歎了口氣。
「妳現在就可以這麼做。」我漫不在乎地這樣回答。
齊歡只是說說而已,沒法真正從她日理萬機的日子抬頭。幾個月後她飛離這座陰冷之島,沒過多久,我去了兩趟柏林。我感覺旅行成功使人暫時分心,而且柏林愛我。
沿著柏林圍牆一直走下去,彎進 Bar25,男男女女漂漂亮亮,在河邊抽菸盪鞦韆聽電氣舞曲晃動雙腳。我沒有朋友,也不是來 party 的,看見蹲坐在深處的老式快照亭,就走進去讓它用閃光為我充電。
坐在路旁等待照片顯像時,有著燦爛笑容的女孩坐過來開始跟我說話,問我從哪裡來,和誰一起旅行。她說自己從未到過亞洲,但她有一個朋友搬到大阪就再也不想回來。她說妳喜歡跳舞嗎?妳不留下來嗎?我請你喝酒、和我們一起回瑞士吧。
那場旅行中,我從 Mauerpark 跳蚤市場帶回一台古舊的 PentiⅡ 相機,一年後才打開機腹,取出原本就在裡頭沉睡的 SL 菲林匣。送沖前我心幾乎不存希望。從網路上仍存的資料看來,東德 Pentacon 的半格機 PentiⅡ 出廠於一九五九年,典金的外殼和秀美的皮套當時令許多女性趨之若鶩,對照使用的 ORWO NP22 底片,加以景中有大雪,我鬆散推測這或許是一九六零代末至一九七零年代初期,某人的冬日回憶。不知經歷幾人雙手幾多時光,送到熱帶亞洲我眼前時長牆已倒兩德親吻,台中西區一名沖片師小心翼翼將它們帶回人間。
倖存的八幅黑白相片似幻似真,有一半僅顯光影,顆粒粗糙卻成像清晰的另一半多是被雪深埋的道路與筆直上攀的樹林,唯最末一張見人影端坐若鬼,我心兇兇跳動。一幀使我感到與掌鏡人最為親近的相片畫面下方橫亙著陽台欄杆,右側有鄰近公寓入鏡,凝視那張相片的時刻我可以清楚意識到攝像者的座標與行動,而當我們終於在視覺向度重疊,彼此的距離卻同時前所未有地被張揚。

我把相片檔案寄給西岸的齊歡,她隨即把自己的電腦桌面換成那不知年月的東德雪中林,然後以手機拍下自己的桌面回傳給我。我反覆看著那回聲的回聲、未料有一日會被我所發掘的日常景象,意識到使我們萬般迷戀、關於情感的記憶物質來自於無敵的時差,那時差經歷到底又完全是官能性的,不在場的人扣下扳機,時光擾動至今。
齊歡在信上說要搬回東岸,「我受夠了加州的陽光。」她簡單宣示,「我的身體需要真正的寒冷。」
我並不那麼瞭解齊歡對溫度的需求,或者其他賴以存活的偏好,我們只一起旅行過一次,到了台東,在無人民宿遇見一名騎偉士牌機車環島的髮型師。他說摩托車是死去朋友的,他向家人商借過來,要達成朋友騎車環島的心願。他身形瘦小,說起話來手舞足蹈,自若地說完這幾乎像個俗氣電影主題的故事,然後問我們要不要一塊吃他剛買的飛魚乾。
「他說的中文為什麼跟別人不一樣? 」齊歡趁他進廚房時問我,「 我都聽得懂。」
「喔,」我笑了笑,「那是台中腔。」
「台、中、腔。」她側著耳朵像在思索。「好像唱歌一樣。」
這次她來,替我把落在她那裡的 Diane Arbus 傳記帶了過來,我沒告訴她我是故意要留那本書下來的,漫長的旅行到了盡頭,我的行李已經太沉太滿,不想法子扔下些東西無法回家。書是在春田買的,我失散二十多年的叔叔開車帶我去,他開會,我則鑽進遊客中心看完林肯的紀錄片。小小的市中心有一間二手書店,我在滿布塵埃的藝術區書架拿下這本傳記,付了錢,然後躺在市政廳的草地上讀書,等他領走我。
我老是讀不完這本書,相較起他人的考證與描述,我對她遺留下來的斷簡殘編更感興趣。在Diane Arbus 過世一年後出版、這位攝影師的首部攝影集《Diane Arbus: An Aperture Monograph》裡,收錄了她一九七一年自盡前夕,在格林威治村所進行一系列講座的紀錄文字,她這樣說過她所拍攝的那些非常人:「他們身上有一股傳說的特質,像童話故事裡阻擋你、並且命令你回答一道謎語的人。」又說「大多數人終其一生恐懼自己會遭遇什麼創傷經驗,但這些人生來與他們的創傷共處,他們已通過自己人生的試煉。他們是貴族。」她所披露的對象在攝影史說不上空前絕後,但正因如此,藉由她的作品你更能夠明白,攝影不僅僅是機械複製現實,攝影是心之眼。如何讓心順暢意識眼中景物,再應運撳下必然使人感傷時間太快或者太遲的按鈕,那便是純粹的現代性,是人與機械之間不可言說的奧義。
石梯坪的清晨,溫柔的日光透進靠海的房間,趁齊歡還沒有醒來之前,我拿起背包裡的相機,為她拍了幾張照片。清醒的時候我們苦於太想親近與遠離對方,那苦太緊,相機無隙可入。快門聲過響,她翻了個身,我們自由來去的火宅裡,僅能在洞穴中以微光勾勒幻影的世界將醒。已將此刻對方投射在心之暗處,我們繼續忍受明日別離。
羅浥薇薇
八○年代出生。台灣苗栗人、左營長大。
現職為幼兒電視轉播與保育員、不自由創作者,未來不詳。 著有小說《騎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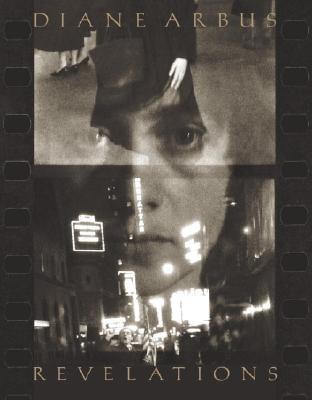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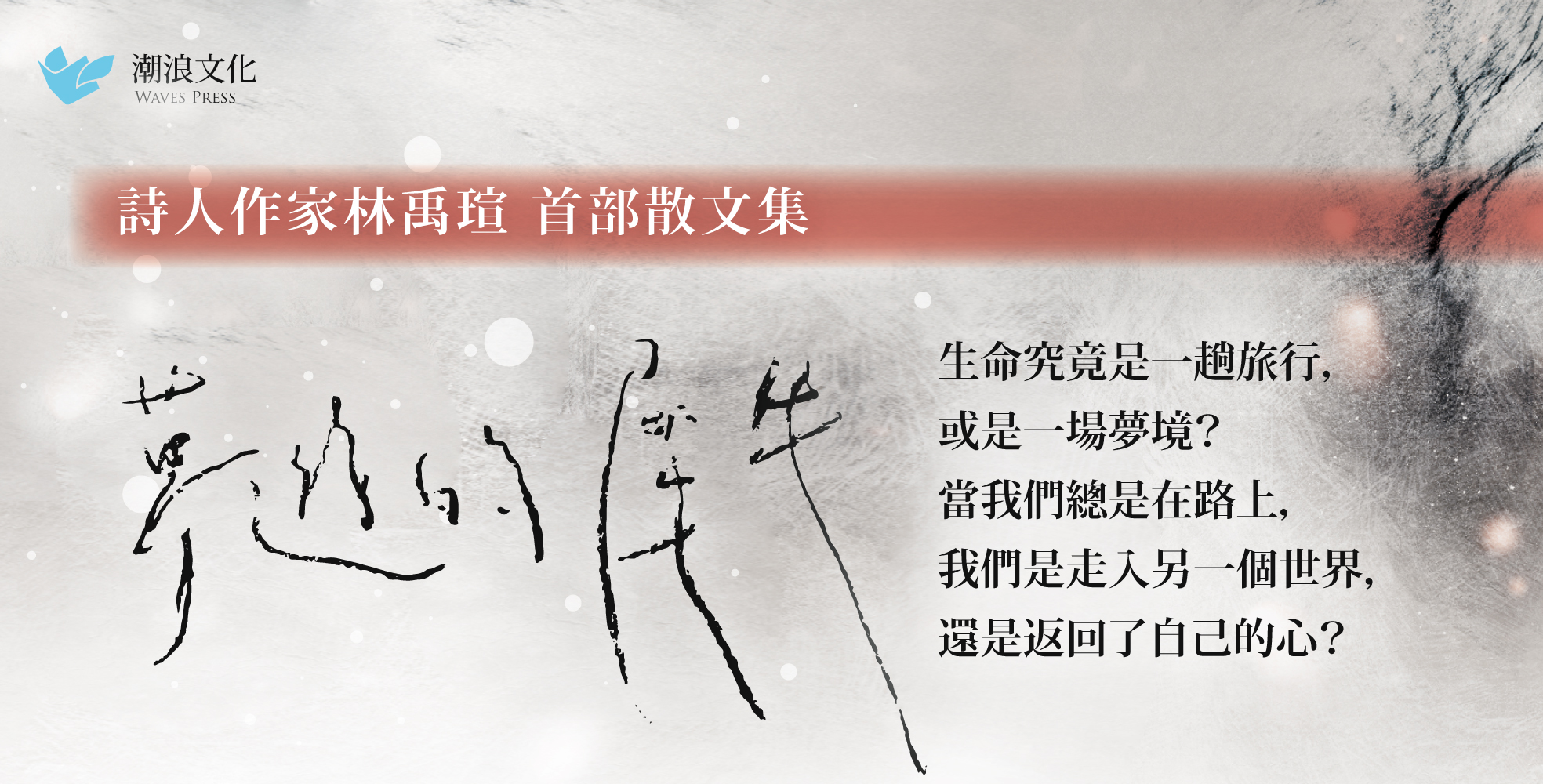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