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生是否就像旋轉木馬,當音樂結束,我們其實哪裡也沒去,只覺得頭有點暈。
在巴黎街道漫步,經常見到旋轉木馬,地鐵站外、三岔路中央、小公園裡,發光唱歌的旋轉木馬是巴黎不可或缺的一景。那叮叮咚咚反覆播放的罐頭音樂、彷彿被迫告別童年的惆悵。不過那些在塑膠馬背上旋轉的孩子們尚且不知愁滋味,他們都在瘋狂尖叫,原來就算孩子以法文為母語,也無法保證他們天生優雅。
在一片人類幼兒製造的混亂之上,繪著小天使圖案的木扉總共八片,用優雅的弧形團團包裹著旋轉木馬的拱頂,圓心中央站立著一匹精壯小馬,滿載希望地,正往蔚藍的天空起躍,他的尾巴雖然看起來柔軟,但塑鋼合金的材質卻不會因微風而飄揚。人造小馬必須了解,牠將永遠屬於這裡,哪裡也去不了。馬匹總與戰勝的慾望連結,小男孩本能地都想騎上最高大的木馬,而安全又乏味的童話馬車是給女生和媽媽搭的。但是無論哪個男孩搶到最棒的動物,音樂結束,黑馬與白馬的距離依然是原來的1.5公尺,大隊人馬其實哪裡也沒去,誰也沒追上誰,拉開那條圍住出口的紅繩,離開旋木光暈,世間顯得有些慘白。

(攝影/何曼莊)
在此刻如此高科技多媒體跨國娛樂的時代,旋轉木馬依然牢牢地座落在每個遊戲場,也許場所的邊陲地帶、也許是托兒中心、也許是一個取代噴水池的裝飾品,雖不起眼,但卻是內心私密珍藏的角落,就算是隨便一個鄉間夜市遊戲場、二流巡迴馬戲班,旋轉木馬比「遊樂場」三個字還要能夠代表遊樂場,它就像冰淇淋的香草口味、洋芋片的原味、咖啡店裡的黑咖啡,不是明星商品,卻決定了場所的基調,它也許過氣了,但是還不能退休。
旋轉木馬在美國常被叫做「Merry-Go-Round」,意思是開心地繞圈圈,這個意象在流行音樂被運用的頻率之高,從金髮微笑牙齒白的流行樂團ABBA、到濃妝長髮重金屬搖滾樂團Mötley Crüe都有這個名字的歌,但大多就像字面意涵一樣貧乏而淺薄,而旋轉木馬的另一個英文名詞「Carousel」,則有比較深遠的典故。
「Carousel」來自西班牙文和義大利文的「小戰鬥」字眼。旋轉木馬之所以用馬為主角,而不是用牛羊或是豬狗,是因為在一開始,這個轉盤上面走的是真馬。路易十四喜歡在夜間的廣場上觀賞「馬術芭蕾」,數大整齊的騎兵隊舉著火炬,騎在馬上,隨著音樂作出整齊劃一的步伐,這是旋轉木馬的前身,而那個廣場就是羅浮宮前的「The Place du Carrousel」,也就是法文中,「旋轉木馬」名稱的出處。
旋轉木馬多麼奇妙,能讓溫馨與悲傷同時湧上心頭,讓狂歡與恐怖相擁起舞。在電影裡面,凡有旋轉木馬的場景,十之八九都會淒慘收場,在那溫暖而微弱的燈泡閃爍下,兒童無邪的笑語間歇傳入耳中,提示著幸福的時光不堪一擊,白色小馬的瀏海隨著音樂起浮,打著波浪努力向前,這是觸發美好舊日的動情機制。《變臉》一開頭就讓主角在旋轉中的(既然是吳宇森導演的,當然要慢動作配上聖歌嘍)木馬上痛失愛子、「家政婦三田」每逢假日獨自到遊樂園點三人份速食枯坐整日、《末路車神》一開場便是Ryan Gosling孤獨(而身材傲人)的背影行經碰碰車、摩天輪、旋轉木馬的兒童世界,來到以命相賭的特技車場,車神從來就沒有明天。旋轉木馬也經常被利用在驚悚片中,大型遊樂園如迪士尼,每年耗費巨資修築更加刺激的遊樂器材,豈知要擊敗雙腳懸空的暗室雲霄飛車,只需要一座失控的旋轉木馬。希區考克電影《火車怪客》(Strangers on a Train)在62年前創造的經典至今依舊無人超越:當旋轉木馬失速,戲也隨著離心力升高而帶往毀滅邊緣,兩個主角在快速飛馳的平台上纏鬥、騎馬的小孩子不知害怕反而興奮不已、旁觀的母親失聲崩潰、勇敢的工人則要冒險爬到急駛的轉盤下方好將木馬停下,穿西裝的紳士只是旁觀並說出一些無用又懦弱的評論。
說到戲劇化,「Jardin d'Acclimatation」是一個十分戲劇化的場所。
位於布隆尼森林公園的東北角,緊鄰富裕的巴黎十六區,占地20公頃,略大於大安森林公園,這是一個有動物的兒童樂園,或者說有很多遊樂設施的動物公園。
「Jardin d'Acclimatation」可直譯為「適應化公園」,它在誕生後的153年生涯中,多次被迫轉型,但無論如何,適應化(Acclimatation)這個字眼從未離開過它的名稱。適應化是什麼?它與「演化」的差別就是,演化可能經歷好幾個世代、多數個體的篩選,但「適應化」是單一動物或植物,在還有命在的時間內,自我調整以適應所處環境的氣候和自然條件,說得簡單一點,就是「服水土」。
「Jardin d'Acclimatation」在拿破崙時代建立,初成立時確實是間研究性質的動物園,但是沒想到,園長在隔年就過世了。
隨後普法戰爭爆發,巴黎在1870到1871年間被德軍圍困,市內糧食極度短缺,饑荒處處,市民甚至連溝鼠都抓來吃,此時屬皇宮所有的動物園內,許多動物想當然耳,就地「為國捐軀」,而動刀的大廚,便是著名大廚Alexandre Étienne Choron,法菜經典的Choron醬汁就是他發明的。
普法戰後,同樣戲劇化的第三共和便展開,而海外殖民似乎讓深受戰敗打擊的法國人恢復了自信,「Jardin d'Acclimatation」再次適應時代與環境,被改裝為一所「人類學動物園」,「展示」來自非洲努比亞、布須曼、和祖魯的部落族人在此地,以滿足此時市民對於異族人類生活的無比好奇,這段Human Zoo歷史,讓本園永遠名列種族惡霸公園的黑名單上,此時才剛步入20世紀。1929年,根據法國歷史學者的共識,這一年是人民在大蕭條席捲歐洲前,還能感受繁華的最後一年。原先為巴黎市政府所有的公園綠地,在這一年,轉移到十六區政府管轄之下。
1950年代,公民意識普遍提升,資料記載過,巴黎市民對公共休閒空間的需求越來越大,於是「Jardin d'Acclimatation」又展開了一連串的整修、改建,包括增加散步道、減少遊樂設施,並且讓「一些鹿消失」,鹿是怎麼消失的,並不清楚,但有鑑於發生在此的歷史事件,怕是凶多吉少。而從1960年代到20世紀末,是當代建築競賽的時代,「Jardin d'Acclimatation」也不例外,園內所剩不多的溫馴動物,靜靜的仰望四周逐漸升起的高樓,那些逐漸遮蓋天際的,都是大師級的設計作品。在四十多年間,這裡又逐漸適應了現代化與消費主義,成為今天的模樣。
2012年初夏,這裡的情景是這樣的:園內假動物跟活生物一般多、水泥面積大過綠地、幾隻水鹿住在鐵網包圍的假山中,在開放孩子們觸摸的可愛動物區,小孩與動物數量是十比一,所幸那些孩子皆髮絲柔細、表情溫柔,洋溢幸福童年的姿態惹人憐愛。這樣可愛的孩子眨著盼望眼神,要求騎馬騎駱駝,你該如何拒絕他、告訴他,如今動物權益伸張的程度到達前所未有的高度,歐洲動物園大多已經廢除騎乘、餵食、表演等「非自然」的觀賞項目了呢?不需要擔心,在這裡你可以盡情懷舊。

(攝影/何曼莊)
付了入園費3.5歐元、購買遊樂票券單次2.9歐元,一次買一本15張票則只要35歐元,還省了8.5歐元。一張票能玩的東西很多,包括可以騎駱駝逛花園、或是騎驢騎馬在場內繞圈圈、或是乘坐顏色十分怪異的旋轉中國龍、或是跟媽媽一起在旋轉咖啡杯上尖叫。來此略盡家庭義務的爸爸,你要是有點不耐,偷偷告訴你,這裡的小賣店裡有賣啤酒。除此之外園區內還有射箭場、鏡廳、小火車、人偶劇場、科學館、美術館,以及一個韓國花園,用以彰顯法韓友誼。
除了遊戲和休閒,此地還提供多種額外收費的工作坊,大人小孩都有,比較引人注目的,是兒童班的課程選單:烹飪、園藝、劇場、魔術、書法、色彩實驗室、香水課、以及名為「Make Up Forever」的化妝課,一時彷彿置身路易十四時代的仕女沙龍,在那裡,他們忙著把自己的子女調教成風騷尤物。
如此懷舊,彷彿一台時光機,試圖抹平過去50年在女性主義和動物福祉面向達成的一切進步,帶我們回到原始本能無限放縱的1960年代,當「廣告狂人」在柯達公司面前提案,那台劃時代的產物,世界上第一台幻燈片輪播投影機,就是1962年上市的「旋轉木馬」(Carousel)。
懷舊感傷(Nostalgia),在希臘文裡意指「舊傷的疼痛」,它比回憶本身還要強烈,它是住在你心中的刺痛感。
這台機器不是太空船,它是時光機。
它帶你回到過去,又帶你前往未來……它帶你回去那些你一想到就心痛的所在,這不是轉輪,它叫「旋轉木馬」,它帶我們像孩子那樣轉啊轉啊,直到回到老家,那個我們曾經被愛的地方。
人總是美化記憶、美化過往片段,那個神奇的機器上面有一個黑色的圓盤,機器前方有一顆灼熱而光亮的投影燈,喀拉一聲,你跟她一起去了遊樂園;喀拉一聲,你們在夏日煙火下初次接吻;喀拉一聲、你們迎接相遇後的第一場雪,拋錨在聖誕節的公路上;喀拉一聲,你們從教堂走出,她的頭紗拖在階上,比陽光還耀眼;喀拉一聲,兒子誕生;喀拉一聲,兒子在動物園見到大象興奮尖叫;喀拉一聲,兒子第一次看到海,你必須阻止他往海中狂奔;喀拉一聲,孩子上小學頭也不回的背影;喀拉一聲,你沒去的學校演奏會;喀拉一聲,你缺席的中學畢業典體;喀拉一聲,你錯過的他離家出走前的烤肉會……在那邊緣模糊的光暈中,鼻中酸楚襲來,你默默的流下淚來。那些平凡無奇的靜止畫面,顏色斑斕、顆粒粗大,總有幾張模糊照片,只因為拍照當下正在開心地玩、正在放聲大笑,雖然模糊,關於那照片的記憶卻分外清晰。那些稍縱即逝的場景:家庭生日會、動物園、兒童樂園、夏末的海灘、院子裡的塑膠泳池,它們總是並行在後悔莫及的flashback中。「Flashback」用中文來說,就是記憶的「走馬燈」,原來用馬拉回人生片段是中西文化的共識。而當那天來到,每個人想到的,必定都是同一件事情--心愛的人。
如果我們要在「旋轉木馬」上放映人生的走馬燈,那個黑色的圓盤能排進140張35釐米的幻燈片,在這140格的人生片段中,多少會有一兩格關於動物園或是旋轉木馬的回憶,告別童年的傷感恰巧是最普遍的一種失落情懷,但是對愛的渴望將繼續如影隨形,直到旋轉木馬的終端,在這個世界上,能夠讓人痛的,也只有愛了。
在我造訪完「Jardin d'Acclimatation」一年多以後,我才從一份文件上,用我坑坑疤疤的法文程度讀到一件重要大事,原來這個園地的所有者是酩悅.軒尼詩——路易威登集團(LVMH),世界最大的精品集團、手提包霸主LV的母公司,而路易威登基金會與世界頂尖建築師Frank Gehry,正在合作把「Jardin d'Acclimatation」的動物園改造成世界第一拉風的前瞻性指標建築,預計2014年落成。
有時候想想也許當這個動植物公園被命名為「適應化公園」時,已經注定了它百年來定位模糊,又不斷被擺弄的命運,即使到了現在,它也以一種粗暴而誠實的美感繼續適應、繼續前行。
作者簡介
曾任《換日線》英語頻道Crossing.NYC 特約主筆。畢業於台灣大學政治系、哥倫比亞大學國際事務學院,曾居北京,短滯東京、柏林,現居紐約布魯克林。著有小說《即將失去的一切》、《給烏鴉的歌》,以及紀實文學作品《大動物園》和散文集《有時跳舞New Yor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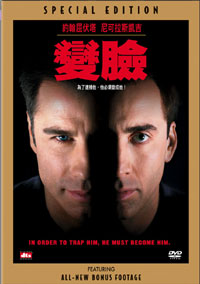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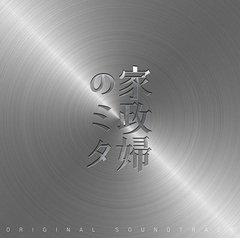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