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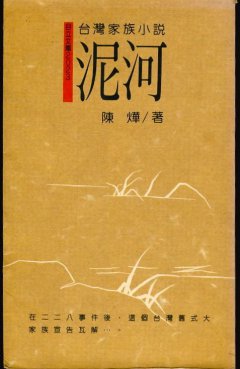
陳燁的小說一方面以呈現歷史聞名,另一方面也以情慾讓人側目。1990年,陳的短篇小說集《孤獨和年輕總是睡在同一張床上》收錄了十餘篇各自獨立、以中學生為主角的小說,其中〈彩虹紋身〉寫一個女同志學生的單戀、〈玫瑰的憂鬱〉寫兩個男同志學生的聚散。這兩篇小說的題目意象(彩虹、玫瑰)對今日讀者而言隱喻了同性戀,不過對1990年代初的讀者來說可能還算是密碼。
〈彩〉的女同志主人翁在初中就愛上一個女同學,但對方卻在畢業後赴加拿大念高中。兩人的分離,與其說是少女的同性戀不被社會接受,不如說是階級差異作梗:主人翁的家庭經濟窘迫,而女同學卻得以到北美留學。但這並不意味她們的環境能夠接受女同性戀;她們並還沒有發展到驚動大人的程度,所以並不知大人的尺度。這段早夭的戀情預告了主人翁在高中階段的單戀:她愛上一個極出風頭的同學,對方不但家境更富裕而且人緣極佳。對方的金錢資本和人氣資本均高,並不會把卑微的主人翁看在眼裡。剛好班上執行的「小天使小主人」遊戲,讓主人翁有機會徹底承受自己身陷暗戀、而對方根本視我為草芥的悲哀。
〈玫〉的男同志主人翁生於權貴之家,身世倒是很像〈彩〉的冷血被戀者。主人翁從小到大都是優等生,無奈一直是體育課的輸家,瘦小蒼白的他也一直不曉情慾。但他在高中(顯然指建國中學)偶遇一個發育良好(第二性徵鮮明)、精通各項運動的同學,一見傾心。沒想到這個體育健將也跟主人翁示好,自願擔任主人翁的游泳教練(游泳,是強烈象徵「性」、「魚水之歡」的運動,在同志文學中常見)。於是專坐特權轎車的(無自主行動力的)和專騎機車的(自主行動力強的)兩個男孩形影不離,直到體育猛男在泳池力邀主人翁裸泳、並且慫恿雙方「圖窮匕首見」——主人翁興奮得昏倒。從此優渥的主人翁留校禁慾用功,而猛男識相轉學到外縣市。
這兩篇小說易讀易懂,但《燃燒的天》收錄的男同志小說就拉高了門檻。《燃燒的天》的出版年只晚《孤獨和年輕總是睡在同一張床上》一年,但企圖心旺盛許多。這冊以「天」為主題的短篇小說集,照陳燁說法是一邊看著梵谷名畫《星夜》的複製品一邊寫成,封面設計也刻意讓人聯想到《星夜》。依我見,「燃燒的天」這個標題幾乎也也可以配上梵谷原畫:天空像是被瘋子所縱之火烤炙變形扭曲。
《燃燒的天》收錄五篇以「天」為題的小說(含男/雙性戀同志主人翁的〈天牆〉),各自獨立,但各自的年屆中年主人翁都有類似的名字(名字內帶「榮」字)。這五個或叫天榮或叫秋榮的中年男子也都各自身陷類似腦袋發燒、身體發炎的不穩定身心狀態。這些男人都有縱火的犯罪傾向。這些男子的身心暴亂狀況都跟他們不可告人的回憶有關,而這些被壓抑、被封鎖的記憶往往來自戀母情結(即,佛洛伊德說的「伊底帕斯情結」)。這些主人翁在小說曖昧的陳述中(曖昧,是因為看不出來是真的發生或純屬幻想),他們好像跟自己的母親(或是類似母親的代理人)發生過「亂倫」關係。但因為這些主人翁的心理狀態不穩定,所以這些亂倫記憶有可能真的發生過,也可能純屬妄想。
既然這五篇小說都展現人心癲狂的一面,那麼其中以「瘋狂男同志畫家榮哥」為主人翁的〈天牆〉就只是狂人故事的其中一篇。如果光看〈天牆〉一篇,讀者可能會覺得作者將男同志寫得太張牙舞爪;但如果將這一篇放在《燃燒的天》全書格局中來看,會發現這篇跟其他異性戀故事相比還算小巫見大巫呢。
故事中的榮哥是個苦悶不得志的、眼高手低的中年畫家,與踏實做小生意的妻子離異,改而被一個崇拜他的小牌攝影家,男同志慶子,所收養。榮哥說起話來比妻子和慶子都大聲,卻也默默等著妻子和代替妻子的男同志去賺小錢養他。他看不起從事商業攝影的慶子,認為自己是孤高的藝術家而慶子只是媚俗者。因為他為了創作而痛苦,所以他追求肉慾的解放,沉迷男妓(按:這點說不通──如果榮哥的生活費都仰賴別人,他怎有錢找男妓?),並邀酒女到慶子的住處親熱,給毫無異性戀經驗的慶子下馬威。最後榮哥仍走不出創作瓶頸,而慶子卻從榮哥身上悟得創作之道,青出於藍,成為被人肯定的攝影大家。
這篇小說一方面在寫兩名男同志,另一方面也在寫年輕攝影家如何超越過氣畫家。在這裡也可看出「伊底帕斯情結」,只不過重點在於恨父(中年畫家)而不在於戀母。
陳燁在〈跋:我看到星群柔和的歌聲〉寫道,「〈天牆〉,它承載了台灣子民的忠實與欺罔,榮誇與屈辱,希望與悲絕,是個授獵天堂卻墮入永劫的寓言。…我… 幾度被主角那憤怒的暴力壓迫得瀕於窒息。」也就是說,作者心不在男同志,也不在藝術家的競爭──這兩種人對作者來說,都是象徵,象徵了貪獵的台灣人民。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比較文學博士。作品曾獲聯合報文學獎中篇小說首獎與極短篇首獎等。著有短篇小說集《感官世界》、中短篇小說集《膜》,以及評論集《晚安巴比倫:網路世代的性慾、異議與政治閱讀》,編有文集《酷兒啟示錄:台灣QUEER論述讀本》、《酷兒狂歡節:台灣QUEER文學讀本》,並譯有小說《蜘蛛女之吻》、《分成兩半的子爵》、《樹上的男爵》、《不存在的騎士》、《蛛巢小徑》、《在荒島上遇見狄更斯》等多種。現為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專任助理教授。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