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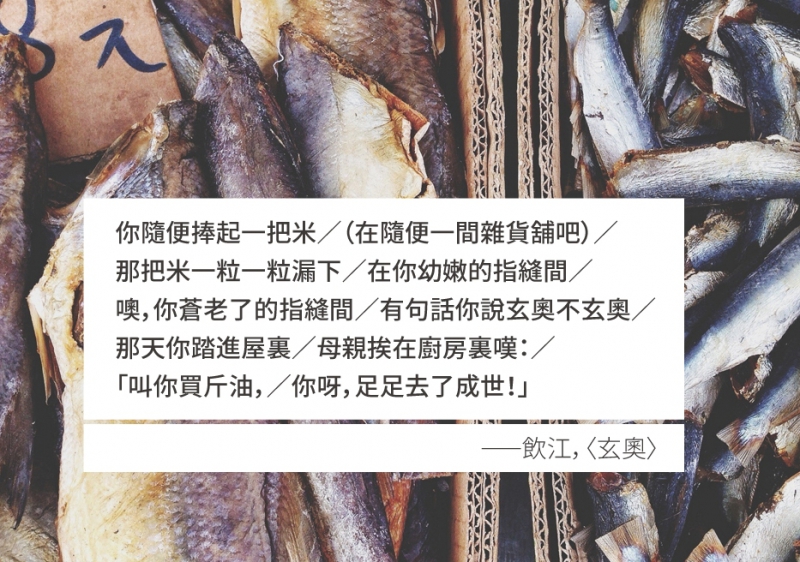
去年在香港跟詩人飲江同桌食飯。他國語非常不順,我的廣東話只能唱歌。相顧傻笑。
即使只是短暫一個下午同在一場朗誦會裡,仍然可以感覺到寫詩的青年們對飲江的敬愛,不少人在他後頭上台,總要接續、提及飲江。廖偉棠在《浮城述夢人》裡寫過,「和他同時出道的詩人洛楓、葉輝也叫他飲江叔叔,甚至比他老的詩人崑南、蔡炎培也戲稱他飲江叔,因為他太符合我們心中一個叔叔形象了,木訥但是很溫柔。」我認真想,還想不出台灣詩壇哪個人會讓大家脫口叫「叔叔」——楊牧叔叔?光中叔叔?(同時浮現前輩們的臉)太不搭了啊。
據說飲江最好的詩以廣東話寫,而且是極為生活的廣東話,不是歌詞裡的雅文字,於是我又有隔,反而不怎麼能抓住當中微妙的啟示。然而,有隔並不妨礙我們接觸異地的詩,點滴洩漏出來都是星光。詩人有些詩為了同語、同文化的讀者寫,有些詩則把門窗開得大一點,於是我也一齊加入。
〈鹹魚店〉(十四行)裡寫:「這鹹魚肉質彬彬的/任誰都會揀去它吧/但它一天天吊在那裡直挺挺的/一丁點兒鹽也沒見掉下來/今天該有人揀去它了/每天早上看著它每天我都這樣想/我每天都這樣想這樣想/漸漸變成了我每天的希望直到/今天老闆過來跟我說/你呆頭呆腦像條鹹魚似的/明天不用上工了」,「肉質彬彬」、「直挺挺」,宛然一條模範生似的好鹹魚,它被吊著、不能自主的位置,與詩中拿來並提的勞動者相似。最後魚沒人買,工也被辭掉了,整日被吊著,也只好呆頭呆腦,牠/他有什麼機會或餘裕可以活動呢?他的批判不像世間一般社會詩,非得把「我正在批判」的牌子曬出,或者非得將意義攞到至明。另一首與鹹魚有點相關的,是〈玄奧〉:
鹹魚在鹹魚的氣味裏游泳/蝦米在蝦米堆上跳/
跳呀跳大海跳飛機/兒時,你背過臉偷放進口裏/
那塊冰糖呢/那塊冰糖/至今仍未溶化/
你隨便捧起一把米/(在隨便一間雜貨舖吧)/
那把米一粒一粒漏下/在你幼嫩的指縫間/
噢,你蒼老了的指縫間/有句話你說玄奧不玄奧/
那天你踏進屋裏/母親挨在廚房裏嘆:/
「叫你買斤油,/你呀,足足去了成世!」
從「幼嫩的指縫」忽然下一句就變成「蒼老了的指縫間」,咫尺光年的魔術,在詩裡是可能的。鹹魚、蝦米、冰糖磊就的雜貨鋪,氣息衝突又豐富,小孩最喜歡盤桓,有時候被媽媽指定了去那裡買什麼,揣著一點錢,就彷彿身堪大任。米從指縫漏下——類似造景從古典延伸到現代,梧桐葉上的雨滴到冷清海濱的沙子,無論漏下的是什麼,都是為了暗示時光流逝。米粒,沒梧桐雨或沙灘那麼浪漫,可是更貼近飲江寫的常民生活一些。詩末,母親那句話原先也是常聽到的,罵小孩買個東西還順便玩耍,放在這首詩裡,卻像是熟年後回望的一句預言,柴糖油鹽蝦米鹹魚,為這些奔忙,也就過了一世人。詩叫「玄奧」,其實講的是普通生活。
最後想提一首飲江流傳甚廣的詩〈我有面頰〉,把愛情裡的動態,「化約」成面頰、嘴唇的「受」與「攻」,製造出卡通般的效果。而遷就與追索之間,最為動人心魄的,並非吻到那一瞬刻,而是閃躲與招引,最貼近時險險飛快擦過,氣流旋轉,花朵全被烘熱——
我有面頰/但求一吻/我有嘴唇/但求可吻
但任我的面頰/如何遷就/任我的嘴唇/如何追索
任轉動的頭/如何飛快/任它們本來/如何接近
※ 香港詩人飲江為「2016台北詩歌節」貴賓,歡迎來聽詩人親自以廣東話讀詩
楊佳嫻
台灣高雄人。台灣大學中文所博士,清華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台北詩歌節協同策展人。著有詩集《屏息的文明》《你的聲音充滿時間》《少女維特》《金烏》,散文集《海風野火花》《雲和》《瑪德蓮》,最新作品為《小火山群》。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