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永遠記得她的表情細緻變換,雖然只有幾秒鐘,但我從頭到尾死死地盯著她,像是看到什麼不可思議的事物。那一瞬間周遭聲音泯滅,她緊閉嘴唇看著我,一張素顏既沒笑也沒發怒,我聽見我背後的朋友一起在叫「李昂老師好!」她聽見了,於是從我的頭殼看穿過去,露出一絲絲像是抹在白色石灰岩上的微笑,微微點了點頭,然後周遭聲音恢復吵雜,她和那一群人沙拉拉地從僵硬如木乃伊的我的身邊晃走了。
明明只是個矮小瘦弱的女人而已,可是與她擦身而過的那幾秒鐘,我卻連呼吸都感到困難,像被地雷爆炸的震波所壓制。我完全嚇壞了,「那可是那個李昂啊!」心裡明明這樣地叫著,可是嘴巴裡卻連一句問候語也講不出來,而且我居然就這樣瞪大眼睛盯著她瞧,一幅「嘿,就算妳是李昂也該認識我」的樣子。
她一走過,我立刻捉住旁邊的朋友,「那是李昂沒錯吧。」
「是啊,怎麼了?」
「怎麼辦,我都沒有跟她打招呼!怎麼辦,她是不是覺得我是個沒禮貌的死小孩!不然怎麼看起來很兇,不太甩人似的。」
「哪有。」朋友說,「是你自己神經過敏吧。」

(攝影/王聰威)
寫這篇專欄文章的時候,我剛剛與李昂以及一群作家從西藏旅行回來。這趟旅行即由李昂揪團,出發前從行程表、辦證件、看旅行門診到要帶什麼衣服,我都一直寫信煩她,到了機場她怕有人忘記帶預防高山症的藥品,特別多準備救急的份量,並且自掏腰包細心買好贈送接待者的禮物。出發後,雖然沿途都有當地導遊、友人相伴,也住在相當好的飯店,但仍然是趟辛苦的旅程。除了應付高山症的威脅,每天都必須五、六點起床,天色仍黑暗之時,就得趕赴十幾個小時車程,或者登山健行的旅途。連我這種算得上是壯年的傢伙都覺得受不了,那一路自稱「本大小姐只適合穿得美美的,坐在高級飯店享受下午茶」的李昂,怎麼可能撐得住呢?結果,大小姐李昂一邊跟著大伙兒喊累,睡覺沒睡好什麼的,一邊卻能在荒山野地裡幫我跟攤販殺價買紀念品,然後在雪頓節當天,她還能跟著如逃難般洶湧人群衝上哲蚌寺山頂看曬唐卡。而我呢,只走到半山腰就被可怕的人潮給嚇壞了,不敢再往上爬,偷偷下山溜掉了。
經過轟轟烈烈生死交關的主要行程之後,有一天早晨,跟她同房的室友,也就是我太太跟我說:「姊姊說她今天不吃早餐,我問她要不要請餐廳另外準備,帶在車上吃,她說好。」
「是不是爬不起來?」我說,「也難怪,這幾天都太早了。」
「嗯……姊姊要我跟大家說她只是爬不起來。」我太太考慮了一會兒,小聲地說,「但其實她是人不太舒服,晚上咳得很厲害。喂,你別說出去喔!」
「為什麼?」我有點驚訝。
「她說,『別告訴大家,我怕他們會擔心,這樣會玩得不開心。』」
於是我想起第一次親眼見到她的情景,心裡有沉甸甸的後悔,那時要是能好好地跟她問候就好了。
這就是大小姐李昂教我的事。
〔李昂作品〕
王聰威
小說家、《聯合文學》總編輯。著有《戀人曾經飛過》《濱線女兒──哈瑪星思戀起》《複島》《稍縱即逝的印象》《中山北路行七擺》《台北不在場證明事件簿》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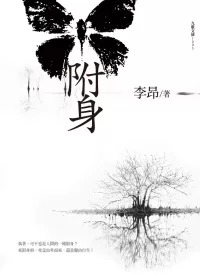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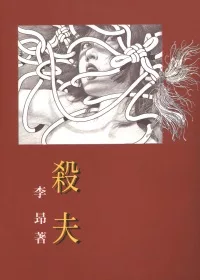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