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決鬥寫真論》與復甦重生
某種程度上,發行於1977年的《決鬥寫真論》可說是《為何是植物圖鑑》的延續表述。在這本與篠山紀信共同掛名合著的傳奇名作裡,中平系統性地以「植物圖鑑」的基本論點,對尤金‧阿特傑(Eugene Atget)、沃克‧伊凡斯(Walker Evans)、威廉‧克萊因(William Klein)與篠山紀信作品進行觀點犀利精彩的批判評價,並對自我做為攝影家的困境與思考,做出頗為誠實自省的獨白剖析。
中平在這本書裡不斷主張,攝影家做為外在世界的「組織者」(此一用語讓人想到激進政治運動裡的「組織者」),若能回歸一個「被動」、「接受」的拍攝觀點,承認事物加諸於我們身上的,那奠基於視覺光學的反向凝視,則其實踐或有可能擾動自現代性以來便與攝影術息息相關的「遠近法」。中平在該書中反覆致意的「遠近法」,事實上即是英文的「perspective」,通常譯為光學原理的「透視法」,但亦可廣義延伸為「觀點」、「視野」「角度」。中平對「遠近法」一詞的使用方式,既指涉了視覺觀看技術之所以成立的單點透視原理,亦有延伸至哲學意涵的個人做為「主體」的視覺性「觀點」或「視野」之意。
以單點透視「遠近法」為主軸的現代性視覺秩序,由於過於膨脹此一「單點」背後的個人主體性,從而誇大了主體對於客體世界的操控與掌握,對中平來說,這樣的視覺建制(scopic regime)隨著視覺技術的發展,逐漸無法妥善闡明物體對於人類的反向光學凝視,原本應是雙向、辯證的主客體交流,逐漸成為主體單向宰制的視覺霸權,這樣的單點透視「遠近法」,因此反而使人類的眼睛「視而不見」地更加脫離現實世界的「整體性」。反倒是從阿特傑與伊凡斯等人的攝影裡,中平看到了攝影家如何將自身改造成面對事物凝視的「接收體」,明白清晰且毫不曖昧地用鏡頭刻畫事物的單純外貌,他並引用華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的「光學無意識」(optical unconsciousness)之說,主張萬事萬物在相機與拍攝者如此「被動」、「接受」的狀態下,得以自動地將所見一切都均等同質、不分高低地呈現在鏡頭下,「讓事物自己說話」。
中平主張在白日陽光下,萬物的外貌光亮明晰,彷彿群起暴力地朝向視網膜衝刺而來,攝影家將這些影像抽離原初脈絡地,轉化為一張張毫無曖昧、價值均等,卻令人覺得有些異樣不安(uncanny)的清晰影像,事實上這種狀似被動的影像拍攝路徑,是將攝影當做一條介於個人與世界間之「緊繃的線」,藉著策略性地區分「自我」與「外在他者」,並暫時棄絕所謂的「私」與「主體性」,攝影者才可能在「被動」、「接受」的影像辯證過程中,重新產生嶄新的感官與自我,中平將此形容為「不斷超越自我存在的永久革命」(又一個出自左翼政治運動的詞彙挪用)。
《決鬥寫真論》發行的1970年代末期,日本攝影正明顯地朝向主觀性、內向性的潮流發展,中平在書中對於篠山紀信的評價極為正面,認為其將拍攝對象全部同等均一化的拍攝視野,與不加區別的凝視方式,如今讀來頗出人意表。不幸的是在1977年《決鬥寫真論》的發行前夕,中平卓馬即因酒精中毒緊急送醫,並造成嚴重失憶與表達能力障礙的後遺症,至今未能完全康復,《決鬥寫真論》因此成為攝影評論名家中平卓馬最後的批判性雄辯文字。對於1980年代後與娛樂產業高度結合、並將寫真集本身做為「物體」大量流通販售的「篠山紀信現象」,或如荒木經惟那樣不斷自稱為攝影「天才」,並持續推廣其似真似假、聳動乖張的「私寫真」觀,究竟中平卓馬會如何評價這些或許與其「植物圖鑑論」頗有辯證餘地的攝影現象?這些問題的答案,如今我們只能自行揣想推敲了。
所幸的是大病後的中平,雖然語言文字不再犀利,但仍奇蹟似地記得其攝影家的身分,並在漫長的康復歲月裡,宛如生理作息般持續規律拍照。他晚近發表的作品,多取材他在居家附近每日遊晃所遇到的環境事物,內容大多是垂直構圖、明亮鮮豔、攝於晴日的彩色照片,並以兩張一組的方式呈現。是否,這就是「植物圖鑑」影像論「類檔案」的具體實踐?或是一種徹底消滅了作者個性,純粹僅是事物反向凝視拍攝者的直觀影像?記憶與言說能力毀壞的中平,是否因為個人的苦難,反倒回歸到一般專業攝影者已經極為疏遠的,那單純素樸的寫真「原點」?
各種評論,眾說紛紜,莫衷一是,而無法妥善言說的中平,如今也無法再給我們解答,但我自己比較喜歡哲學家淺田彰的詮釋。他觀察到中平新系列的彩色照片,即便具有圖鑑式的驅力特徵與排列特色,但其垂直構圖的影像景框,總不是那麼樣地工整方正,而是帶著些許地傾斜歪曲,彷彿按下快門的一瞬間就要跌倒般,或如植物的莖葉搖擺於風中。這樣的影像,因此既非純主觀視野的呈現、亦非客觀世界的被動反應,而是兩者互動、充滿機遇的混合體,體現在一個尋求康復的攝影家,每一天藉由影像與世界重新「相遇」的道路上。
從最早的攝影實踐裡,中平便明白宣示,攝影是不可能在一瞬間就掌握住整體世界的複雜面貌,但在寫於攝影集《Adieu à X》(1989)後的短文裡,他言簡意賅地陳述自己病後康復的心境,正如每天必抽的Hope牌的短菸,就是抱持著「簡短微弱的希望」(short hope),藉由攝影認真地活下去,藉由每天簡短片段地拍攝,或許總能逐漸趨近那雖然遙遠,卻值得追求的世界「整體性」。
我想起在森山大道的成名作《日本劇場寫真帖》(1968)裡,有一張以連三格底片放樣的中平卓馬側拍照,影像裡的他一身勁裝,帶著角架在街頭獵影,讓人聯想起俄國導演維托夫(Dziga Vertov)在《持攝影機的人》(Man with a Movie Camera)裡,對於拍攝者與攝影機合而為一,人眼與「電影眼」相輔相成的視覺意象;而在《決鬥寫真論》裡中平不斷談到自身做為開放、被動的「接收體」,甚至在名為〈插曲〉的「燒相片」短文裡,提及自己就像一個木頭節孔,彷彿暗箱相機(camera obscura)的透光洞,上下顛倒、正反不分;而在攝影家Takashi Homma向中平致敬的錄像作品〈Short Hope〉(2011)裡,觀眾必須走進一片漆黑、明顯在指涉暗箱相機的房間裡,看見螢幕上不斷地以火柴點燃Hope牌香菸的中平,如何讓暗箱裡出現一絲微弱短暫、卻倔強實在的火焰。
 暗箱相機的成像原理(圖/wiki)
暗箱相機的成像原理(圖/wiki)
中平卓馬,被稱做「變成相機的男人」,好像許多人仍難免要如此浪漫地去想像做為傳奇的他。
只是「火焰」,如今不再是60年代末激進「風景論」裡都市反叛的象徵,亦不是70年代摧毀相片時自我棄絕的虛無烈焰,短暫卻實在的「希望」,取代了全面革命的激情與自我懷疑的灰暗,那絲黑暗中微弱的香菸火絲,與呼吸吐氣的開闔,其孤高彷彿一台老相機的快門,實在、乾脆且倔強。
張世倫
藝評人,攝影研究者。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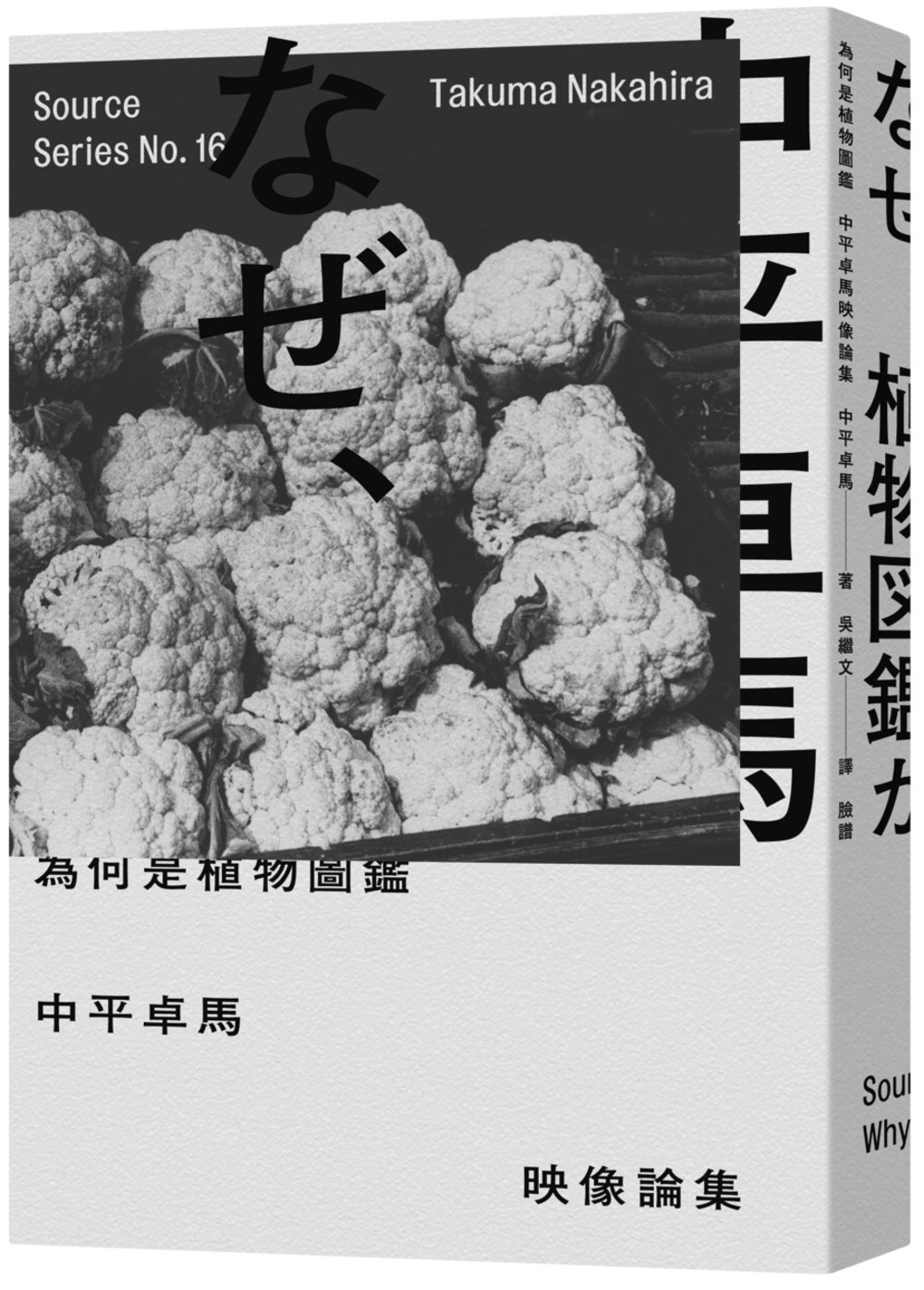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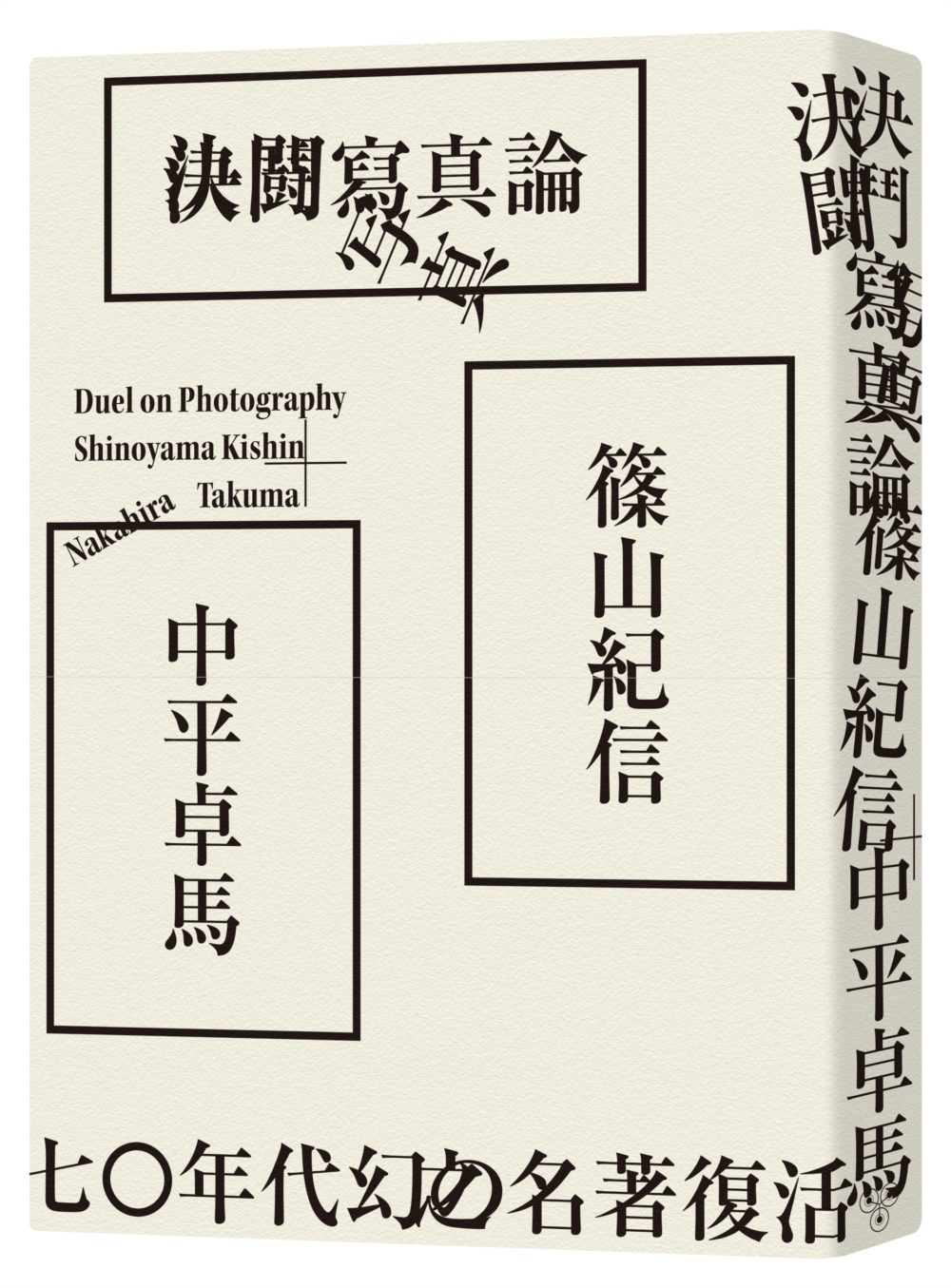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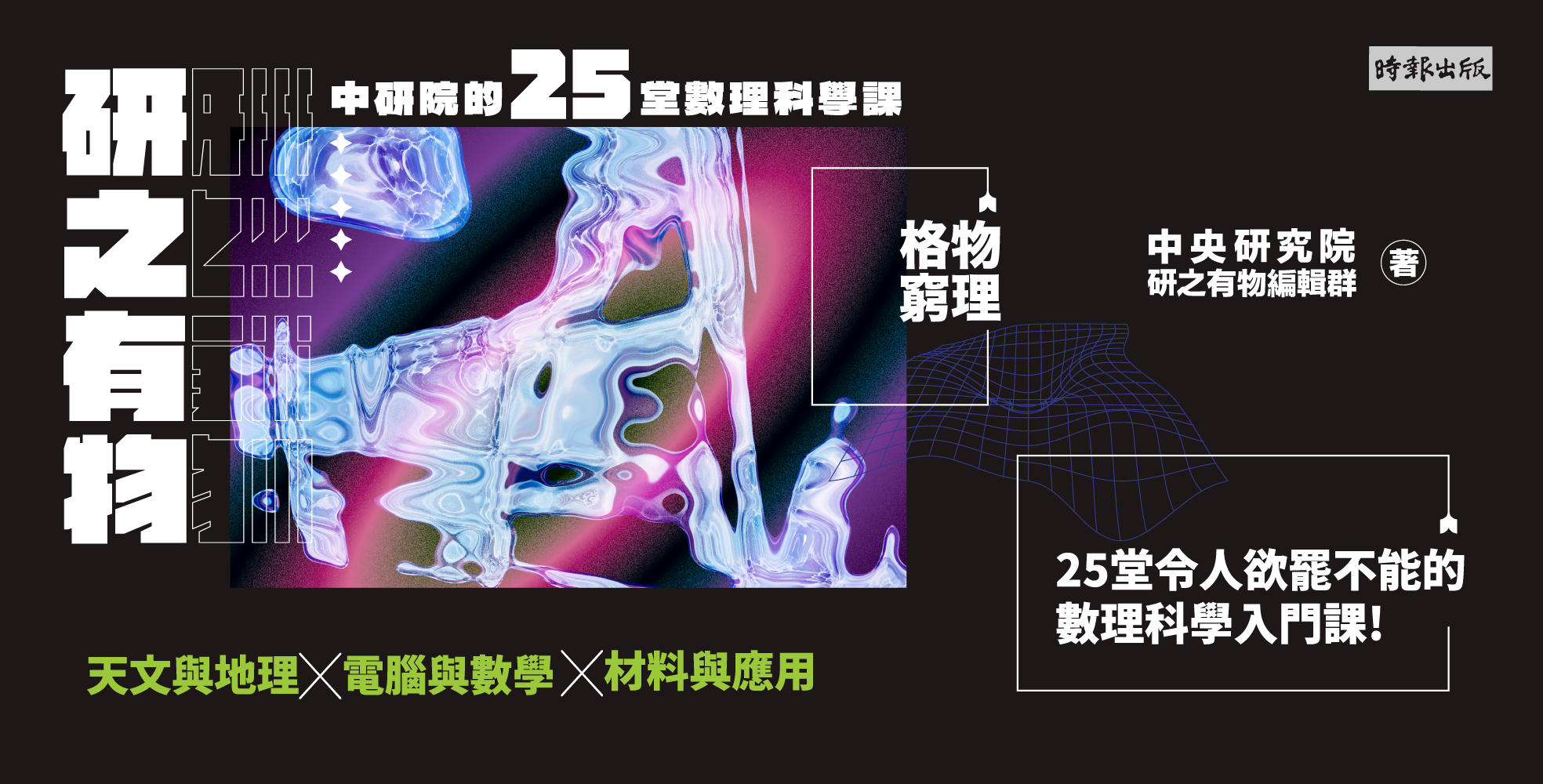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