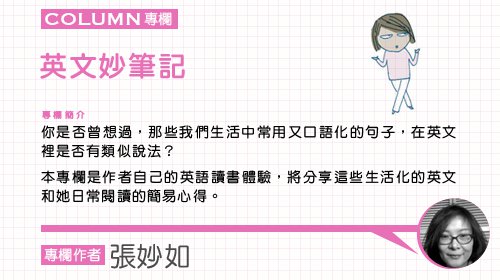
〔接上集〕
黑人天性有比較溫順,體格比較弱小,運動神經較不發達嗎?沒有沒有沒有。那為什麼白人可以奴役到黑人?最精簡版的答案是:武器。一對一的肉搏,白人應該不會是黑人的對手,但如果白人有槍黑人沒有,黑人不會是槍的對手,擁有武力就有權力,武就是權。世界上最懂得這個道理的人民我覺得是美國人,這也是為什麼美國常常發生槍擊事件,政府卻一直很難從人民手中奪走擁槍權──殺人的從來都不是槍,而是身後扣板機的「人」啊,所以該禁的怎麼會是槍?而如果壞人怎樣都能弄到槍支,好人怎麼反而要被奪去合法的擁槍權!
世界上多數國家政府都禁止人民擁槍,說好聽一點是為了大家的公共安全,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這又何嘗不是以某種美名為藉口,變相削弱人民的權和力?除了一些全民皆軍的戰亂地區之外,在太平地區裡,對人民禁槍越嚴重的國家,往往越是極權之地。請不要那麼高興你處的地方禁止人民擁槍,請不要以為那叫安全、治安好,不要被假神聖教得自廢武功還覺得那是美德或公道,這地球畢竟是個「有心人治」的世界,不是神治。
漢娜剛到非洲時,她很訝異為何那些陌生的黑女人會那麼照顧流產的自己?──別忘了,漢娜是個瑞典鄉下來的赤貧女,別說她不知道世間有黑奴這回事了,她原本在瑞典還是個文盲!完全沒有先入為主的觀念的她,是來到東非之後才漸漸開了眼界,才漸漸學知這黑白有別的世道,雖然她曾一度想過這不公平,可是她也曾一度享受著高人一等的美好滋味,在她心中,這天秤的兩端總是不停地互有起伏,一直到,她親眼目睹了一個黑人太太殺了她那欺瞞不實的白人丈夫的案件。
白人死者是她已故第二任丈夫的舊友,丈夫生前曾提過此人是個「可信賴」之人,當時黑白配極為罕見,所以連漢娜原本都以為死者是個值得信賴、打破種族界線的良人,因此想要轉手所有產業回瑞典的漢娜,才會數次去尋求此人的建言。漢娜在某次去拜訪這名友人時,正巧撞見一票人在爭執,原來這個可信賴友人早就成家,他把原妻小安置在另一城市,卻在洛倫索馬貴斯和這個黑女人另外結婚生子,這天他的白人妻兒突襲來訪,這個黑妻才知自己被騙婚,不甘被騙的黑妻在衝突中怒殺了丈夫,下場當然是立刻被抓入獄,黑人殺白人連受審都沒資格,直接就是死罪了。
漢娜在東非生活最不適應的點是,這裡似乎是個「只有謊言的世界」,白人朋友總會提醒她,黑人都愛撒謊不可信,可是她也覺得白人往往騙更大,重點是:白人欺世盜名無罪無事,黑人求個實卻要付出生命。漢娜於是決定,她要這名被騙、但忠於己心的黑太太被無罪釋放!
漢娜並不知道自己弄了個多艱難的任務給自己!別說黑人殺白人直接是犯天條,要幫那個黑人找律師,也是大家聽都沒聽過的破天荒!雖然她已是巨富權貴,卻找不到一個白人律師肯接此案,甚至獄官都直接告訴漢娜,黑人絕無受審的資格,就算她終於找到一個肯接案的律師,黑犯連見律師面談的資格都不會有!更艱難的是,這個黑太太自己寧願死也不願接受審判,她只願意在自己的靈魂(逃出獄)和死亡間二擇一!這也是個動人的決定:誰要謊言連篇的虛假世人的審判!
表面上,這本書只是在講一個瑞典女子在一百多年前的故事,但其實這本書我覺得牽扯到的議題相當多啊!百年後的今日,你試著去奴役命令街上遇到的黑人看看,我想你會被打殘吧!(而且打你的可能只是看不下去的路人,而不是該黑人)可是百多年前,黑人天生就是賤民,就是奴僕,就是沒有自己的人權。真不敢相信,有些人只是要當人,就得經過數百年的奮鬥!因此我真心為同性成家的權利感到憂心!一百多年前白人奴役黑人就已是持續數代的天經地義,就像現在那些不知道自己很可笑的,為傳統家庭價值的外觀而拒認非我族群者應有的權利的那些人一樣。請別再提自然了,如果沒有文明先進非自然的武器,黑人天生之資就不可能是奴!(請別說智取也是自然的一部分,發明槍的聰明人也只是一人,或一小票人,可是隨後任何笨白人也都能持有並使用,這明顯已脫離物競天擇的自然範圍),再者,先進的設備或藥物,早已普世地延長了人類自然的壽命,人工受孕至今更是普遍,人類早已有違反自然天命決生死的能力,這些也都不限於發明者或其團隊獨享,請問,自然在哪裡?
所以我就說我不是太愛讀賀寧‧曼凱爾的「非韋蘭德」的書,它們總是讓我靈魂覺醒又只能感嘆蒼生……想一次就有一次的痛,尤其看到號稱萬物之靈的人類其實總是在殘害著萬物和自己,「靈」在何處?人人最非凡的旅程真的只能在沒有時間和空間的內心深處嗎?果真如此,漢娜又何必走這麼長的艱辛路去營救一名黑女人和她自己的靈魂!在內心想一想、痛一痛,不就得以無愧,得以非凡、了事了嗎?!
一切在很久很久以前,就已經不再是天決,而是我們的己意啊!就別再用盡藉口去欺世盜名了吧。
Perhaps the commanding officer can be bribed?
或許這指揮官可以被收買?
For him, God is someone who hands out punishment─the same God that my grandmother in Funäsdalen used to talk about. He believes in the same hell that she did. He's not like me. I don't believe in hell, but I'm frightened of it all the same. If there is a hell, it is here on earth.
對他而言,上帝懲罰罪人──和我在Funäsdalen的祖母生前信的是同一個上帝。他也相信我祖母所相信的同一個地獄。他和我不一樣。我不信地獄,雖然我同樣會被它嚇到。如果那裡真有一個地獄,它就在這人間。
God is white, Ana thought. I suppose I've always thought that, but never so clearly as I do now.
上帝是白人,阿娜想。我猜我一直是這樣認為,只是從沒像現在這麼清楚。
All she did know is that just now she had the upper hand.
她知道自己剛占了上風。

張妙如
從服裝設計跳到漫畫家,再轉而興起圖文創作的潮流,近年更嘗試寫偵探小說。著有《交換日記》、《西雅圖妙記》等,作品風格走輕鬆休閒路線,耐看又帶著時髦感。現今旅居西雅圖。最新作品為《交換日記15》《西雅圖妙記7》。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