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的野心:十九世紀英俄帝國中亞大競逐》這本書讓我不由地想起《馬可波羅東遊記》,儘管兩本書在本質、敘事背景的時間與內容上有著天壤之別。我之所以有如此跳躍的聯想,其實與本書作者彼德.霍普克(Peter Hopkirk)生動的敘事手法不無關係。
在本書中,霍普克引用了大量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史料,經過縝密的整理與分析後,他以流暢的敘事手法,讓大競逐史上重要人物的經歷躍然紙上。我們彷彿從書中看到本恩斯爵士進入布哈拉的意氣風發,也可看到史多達特與柯諾里被納斯魯拉囚禁在「黑洞」的慘狀。而那一場又一場、從土耳其到西藏的戰爭中,在霍普克筆下也不再只是文字,也讓人在閱讀時隱約聞到那逐漸濃烈的血腥味。
霍普克在本書開宗明義寫道:「在過去的一百年裡,這個世界其實並沒有改變太多……這些事件,對生活在維多利亞女王時代的人來說也並不陌生。今日的頭條新聞,確實經常和一個世紀、甚至更久以前的沒什麼分別,但人們卻沒有從慘痛的歷史學到教訓。」當我們在2022年的今天讀1990年霍普克所寫的作者序時,可驚訝地發現到,至今其論述仍十分深切。
正如同霍普克書中提及的:「如果俄國在1979年12月時,還記得英國於1842年曾在阿富汗面臨過相似的處境、以及當時他們慘痛的經驗的話,那麽俄國也許就不會落入相同的陷阱,而犧牲一萬五千名士兵的性命——更不用說無辜受害的無數阿富汗人。」「莫斯科太晚才發現,阿富汗人其實是難纏的敵人,他們不只依然保持高昂的戰鬥力(尤其是在他們挑選的地形之上),還快速地學會了最新的戰略部屬。」當2021年8月美國從長達二十年的阿富汗戰爭泥淖中撤出時,是否也適用以上觀點?可見在不同的時代裡,歷史總是一再重演,也往往有驚人的相似性。
阿富汗人不論是在十九世紀面臨英俄的相繼入侵,或是在二十一世紀以來與美國的阿富汗戰爭,他們大都是無辜的(特別是一般平民百姓),如果說有什麼能讓阿富汗人拿起武器拋頭顱灑熱血拚死抵抗的,大概就是對自主性、宗教教義的捍衛此兩大課題了,這可以從英國短暫佔領阿富汗首都喀布爾的歷史看出。當十九世紀英國人在阿富汗建立以舒賈沙赫為首的魁儡政權之後,「阿富汗人對英國人的恨意一直不斷上升」;反觀英國人則將充滿異國風情的喀布爾作為度假勝地,連昔日刀口舔血的本恩斯也鬆懈下來,將自己形容為「一個坐領高薪的閒人」(a highly paid idler)。此外,當時英國人似乎已將喀布爾視為新家,紛紛將家眷遷移至此,同時許多英國人開始在喀布爾與當地女性交際調情、飲酒作樂,這對普遍身為穆斯林國家的阿富汗大多數居民而言是很嚴重的冒犯。
阿富汗不過是英俄大競逐歷史中一個區塊,也就是在整段大競逐的歷史中,牽扯的民族不只阿富汗人,還包含隱伏沙漠的土庫曼盜匪、逐漸衰微的鄂圖曼帝國與滿清、居住於西藏高原的西藏人等,而每個民族在這場英俄大競逐的棋盤中,都好似一顆顆身不由己的棋子。
當我們在進行歷史討論時,唯有站在那個時代人們的角度思考,才能不落入抱持後見之明、以今非古的謬誤當中。身處二十一世紀的我們,在透過《帝國的野心:十九世紀英俄帝國中亞大競逐》這本書瞭解十九世紀的英國人與俄國人之時,或許會覺得英國人對俄國人野心的擔憂是多慮的,但別忘了本恩斯、璞鼎查、波廷格、本那比和羅林森等人身處的十九世紀,是充滿帝國自信、毫不掩飾愛國主義,並堅信基督教文明比其他文明優越的時代,因此對他們而言,俄國對印度的野心是再真實不過,而且一直都存在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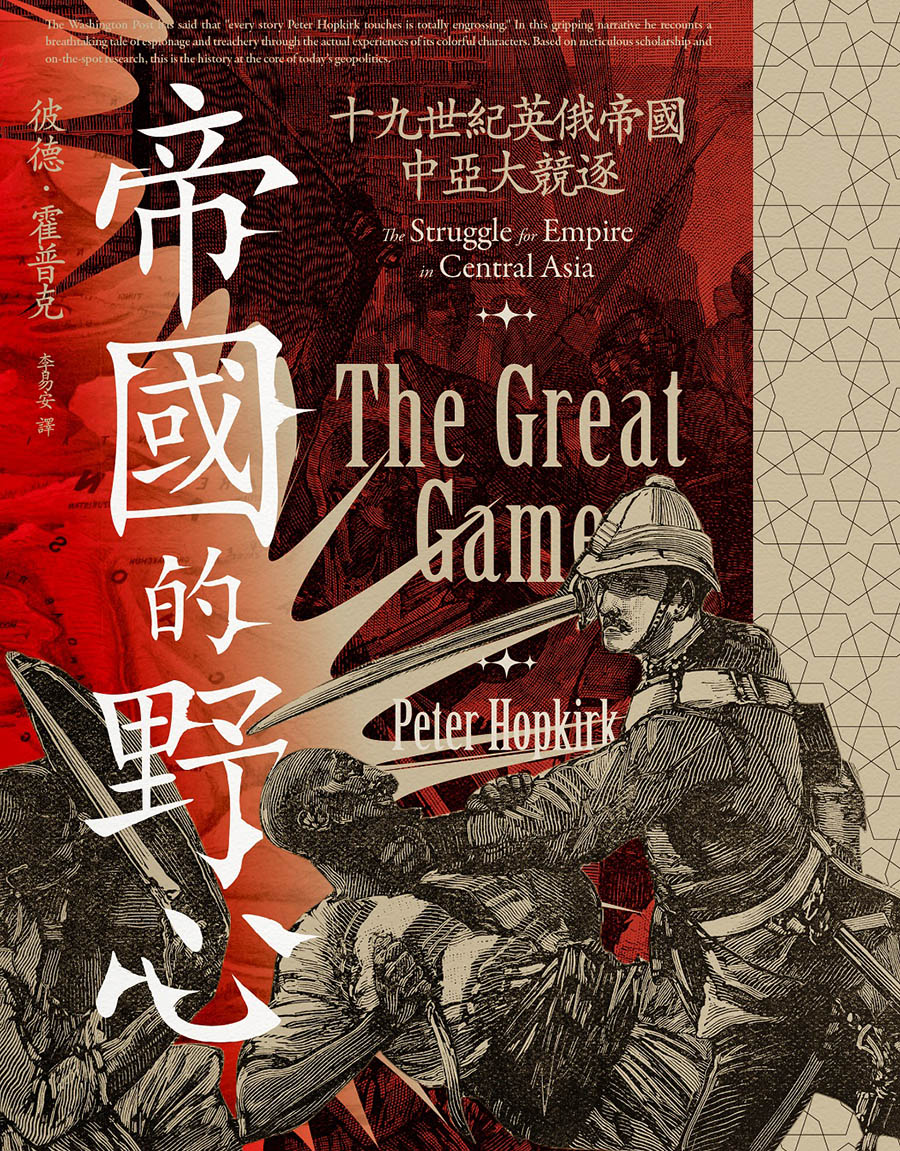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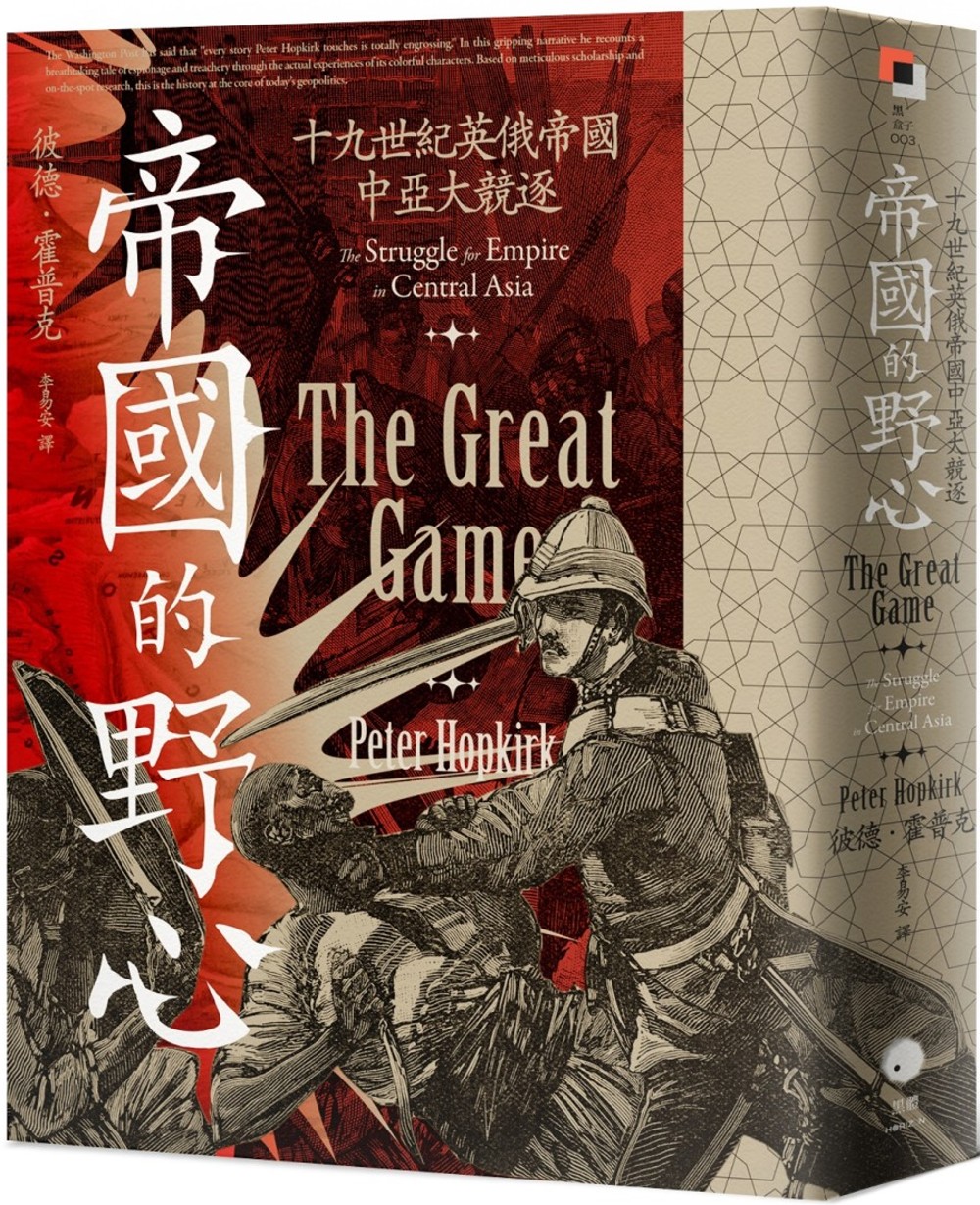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