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一次讀阿尼默的圖而失望。平日他接受副刊邀請繪製插圖,像限制較少的翻譯,先讀懂了另一人作品,用自己的話/畫再說一次。但豪氣宣稱「我沒想過不畫畫,我就是要畫畫」的他,不僅總是變換風格、施展魔術,還能寫極好的文字。雖寫得少,又自承很懶,卻有野花野草那種天生天養的美。結合兩項特技,歷時三年,終於完成《小輓》。
《小輓》共三首曲調高低的哀歌,從〈旱溪〉藉孩童視角旁觀一日間紛紛的死,確確實實的「小輓」;變奏為〈家蚊〉的「小挽」,一對夫妻面臨逝去、無法承受的不捨與「挽」留,亦是夫妻關係瀕危終又重新「挽」手前行(當然,他們在山中滿樹的果實也是用「挽」的);再至單身女子回憶戀人為她編織辮子,那甜蜜的「小綰」,當時間鮮豔的〈緞帶〉鬆脫,彼此握住的手鬆脫,曾被綰結的一切俱往矣,只能將自己填入巨大的,愛的空洞。
「旱溪」為台灣中部河川名稱,亦指一區域,因雨水豐儉不定,乾季乾涸,故得名。成長於此地的阿尼默,挪做篇名,成為隱喻。〈旱溪〉運鏡靈活,先透過乘客手中的報紙,電視播放的新聞,詭異搭訕的路人等畫面,誘使讀者誤以為主角即是被綁票的小孩,漸漸才得知「綁架」小孩的是小孩自己:藉一場車禍,從生活動線逃開,順勢導覽了1980年代台灣鄉土:候選人看板,老巴士,變電箱,大佛,檳榔攤,公共電話,柑仔店……當小孩半日流浪,終於鬆一口氣,坐上河堤,用養樂多向落日乾杯,場景旋即切換為烏鴉分食死犬,這自然引人想起當車禍發生,眾人圍觀傷者的畫面。小男孩白紙般的心由此染上顏色。
我喜歡那嗜血如被夕陽潑紅的一幕:犬之死,餵養著烏鴉的生。我也喜歡當小男孩返家,無人知曉他的「逃亡」,他望著睡在椅上的父親,小心翼翼用手指感應父親鼻息——死亡,原來可能離我們這樣近。經歷這一天,他的生活再不是只有無狀萌生,某一條久旱的溪,此刻忽然汨汨流出水聲。




〈家蚊〉前所未見指派雌蚊當女配角,結果簡直張曼玉巧笑倩兮在林青霞身旁一般搶戲。當成為母親的女人,親暱哄睡嬰孩,時間到了就餵奶,交配後的雌蚊也將數以百計的卵,誕產在有水的地方,比如隔著紗窗的盆栽,很快孵化,成為家蚊。母親為了孩子展開電蚊拍保衛戰,揮之不去的卻是耳邊嗡嗡聲,是藏匿屋裡,似有若無持續閃動的黑影——奇特的是,家中雖有新生兒降臨,那對理應是新手父母的男女,卻時時溢出難以掩抑的哀傷。(極好的)謎底揭曉之前,大自然的繁殖和人類的繁殖互有消長,一如〈旱溪〉有烏鴉啄食死犬,美與恐怖並置,阿尼默圖畫的敘事中,似乎透露一種屏除人類中心主義的傾向,其生命觀或許就透過其環境哲學來呈顯。但傑出之處又在於絕不說教。當哀傷煙散,女人決定離開屋子,迎向新生活,女配角的戲還沒完:女人踏出家門那一瞬,雌蚊飛快地在她頸間,叮出一個小小的墳。




〈緞帶〉描述一名女子在尋常生活裡,被往事砸了一身,一條橘紅色緞帶勾起情傷,而憶起自己曾追愛至異國,尋人不獲,羨慕他人的愛情。在彼多風地帶,緞帶甚至被吹遠,她一路追,想起情人信上寫,「風扇在轉卻感覺不到風」,這說的是愛情嗎?以及,「聽說有種候鳥再也不從這裡回家了」,這說的是情人自己嗎?相較前兩篇,情節更簡潔,情緒卻像等待被稀釋的詩。跋涉失戀的艱難,從不亞於任何一種死亡,正是愛的死亡,使緞帶彷彿得了生命,記憶如活物,劈開暗中枯木,裂出生命的空墳。我想起騷夏的詩:「將一顆時間汰換的乳齒/向黑夜投擲/讓熟悉的山頭於是有墳 」。
墳,是靈魂安息的小丘,是悲傷如煙纏繞的家屋,也是往事消亡的空繭。《小輓》三篇,分別可見墳塚印記。阿尼默在各種憑弔手勢中,往往使故事情節經歷從白日到夜晚,藉某一逝去之物的提醒,反向指出了生活與生命的活潑與野蠻。而那正是,唯有時間的黑影犁過,無差別的殘酷慈悲都已通過,才能得到的禮物。
作者簡介
延伸閱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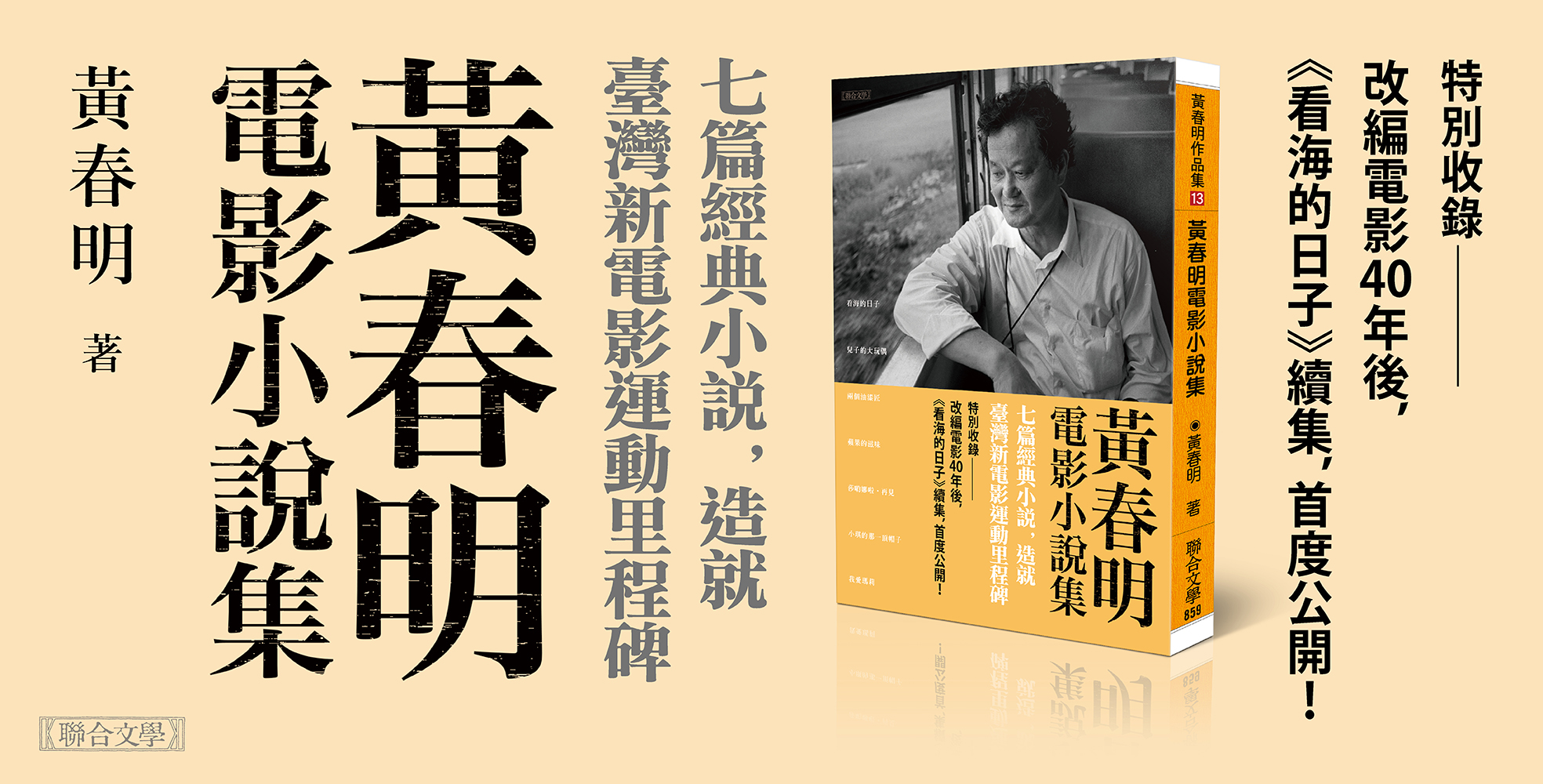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