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攝影/但以理)
初見賴鈺婷,一時以為見著了日本女星小西真奈美。
淨白的眉宇,嘴角一抹親切的笑,你覺得她該是細膩柔弱的。話匣子一開,在她的言談之間,你知道她的確是細膩,也的確是多感溫柔,更是平穩而堅韌的。
也許這跟她擔任教職有關,畢竟在書寫的身分之外,更多時候,她必須面對許許多多或乖巧或頑強的青春學子。也許,跟她近年來接連遭逢父母離世的遺憾有關,如果說人總是等到失去些什麼,才會醒覺想要尋回些什麼──這似乎正是賴鈺婷決定離開生活十年有餘的台北、返回家鄉台中的原因;也成了她花上兩年多,四處遊走台灣各地小鄉小鎮,寫就《小地方》一書的緣由。
「我跟這個世代的很多人一樣,從高中就離開家,到別的城市求學、工作、過日子。以自己為中心往外發展,試著獲得別人的認同。」在離鄉打拚的歲月,賴鈺婷也與諸多遊子相同地,將父母落置的排序漸次往後挪。「一個離鄉者,一心一意只在追尋自己目標或理想,其實是把這些拋諸腦後的。」及至父母相繼纏綿病榻,賴鈺婷開始週末通勤返鄉陪病的日子,週復一週的往返,她驚覺自己在親情的部分,有著很大一塊的空白。「那些累積下來的高鐵車票,讓我慢慢生出一點點不同的想法,想要好好抓住、記憶住我可以記憶的東西。」
2006年,賴鈺婷以《彼岸花》一書正式踏入文壇;推出這本作品之前,她已先後獲得多項文學獎,被譽為最具潛力的六年級新生代作家之一。相形之下,《彼岸花》的情緒流轉多於《小地方》,較為個人,也更顯隱祕。六年後的《小地方》,筆鋒一轉,由書寫自我轉而記錄眼下,更為貼近土地與生活。賴鈺婷讓自己跳出同世代散文書寫者多半關注的「私我」,把視野與焦點移到小人物、小角落發生的事件,不若黃春明、劉克襄的根植斯土,反倒像是帶著一點距離、以好奇探尋的眼光往返巡逡,期望從中找到自己得以安穩落定的原點。
「之所以會有這樣的轉變,一方面是自己情感的因素,再者也是希望自己可以試著跳脫,想要『離開一個既定的模式』。」
賴鈺婷選擇在父母過世數年後回返家鄉,看似沒有什麼必然的遷移理由,然對她而言,彷彿是一種昔日的撿拾,也是她選擇用以檢視過往的方法。《小地方》中的〈芒種 臺中.大里 七將軍廟〉此篇,則是賴鈺婷最大的轉折點。

(攝影/但以理)
「那個時候發現,自己嘴上老是講著什麼『回到故鄉』之類的,看起來像是回歸,回去之後才明白,正因為父母都已經去世,自己跟『故鄉』的連結,幾乎是等於零。」賴鈺婷認真回想,對眼前這片出生成長的根源地,其實只有高中之前的記憶;而這一區塊的記憶,又因為中學時期的升學壓力,被壓迫得慘淡非常。「台中是我的家鄉沒錯,但我覺得這是定義上的東西。當父母都不在、回到那個『我覺得我應該很熟』的地方時,才發現自己真的很像一個家鄉客。」因為獨立生活以來的一切日常都在台北,與原生之地反而顯得格格不入,「甚至你怎麼樣跟人解釋,在這段抽離的時間裡,你是什麼?」
結果,家鄉卻成了異鄉,化為促使她一再離開的力量。「我的回歸,反而像是流浪到家鄉一樣。」驚覺自己對於原本以為的熟悉之地竟是如此陌生,賴鈺婷興起了四處遊走、重新探訪的念頭,「我好像是想在這裡頭找一個情感跟記憶的連結。」這是她最剛開始的動機。於是她從腦中挖掘,以幼年對父母親族的相關印象為起點,想到什麼、記得什麼,或遇上什麼,就成了出發的驅動,要她往各個鄉鎮角落延伸。例如去到苗栗尋一只茶壽,或逢見龍眼盛產,憶起霧峰的龍眼山,在那裡拼湊家人們曾有的足跡身影。景物或在,人事已非,卻可憑藉文字轉為永恆。「我想透過這些篇章的書寫,把發生在童年或成長過程與父母相處的片段,以及一些對於景物的看法,再做一番爬梳。」
於是每一次的離開,都成了一次暫時的跳脫,也是一次新的回返。「我好像帶著一點自己個人情感,去走踏一些地方;在那個今昔對照裡,的確也企圖找到過去斷裂的親情的連結點。」然當下所見,卻又不只如此。或許也可說是無心插柳,但對賴鈺婷而言,原本她只是想要完成一些什麼,卻在尋覓的過程中,又發現了一些新的什麼,有些關於他者,有些關於自己。「旅行的過程像是一種自我對話,會讓你問起自己行進的意義。」她彷彿啟動了塵封已久的定格畫面,讓這一個又一個的「小地方」,不再只是到此一遊的記憶之地。
「我其實不知道我的讀者在哪裡,也不確定有多少人會對我寫的東西有共鳴。」賴鈺婷淡淡地笑說,她寫的不是什麼難以企及之處,有些地點甚至就在你我附近,真要移動,也不過幾個小時的距離。但看似平凡的書寫,都是她真切的感動,所以格外想要傳達出去。「它可能不代表什麼,可是這點點滴滴收集起來,我的旅程才是真正完成,變成我生活的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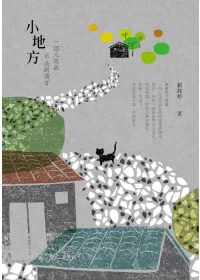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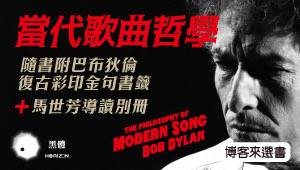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