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禎和(1940-1990)的作品很少被當作同志文學看待,可能因為他都將同性戀寫成作品的配角而不是主角。然而,這些配角喧賓奪主,例如,王禎和代表作《美人圖》 、《玫瑰玫瑰我愛你》描繪男同性戀性幻想,都是嗆辣詼諧的例子。同志文學領域應該把這些配角當作資產納入,而不該僅僅因為不是主角就加以排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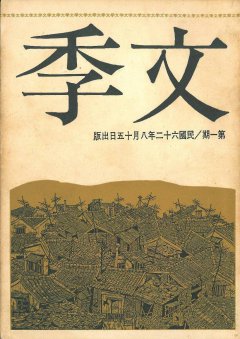
《文季》雜誌書影(提供/紀大偉)
《望你早歸》長期被人遺忘,近期卻又被記得,是因為它曾經被查禁,解禁之後重新搬上舞台。遭禁是因為「望你早歸」這個劇名被讀做政治諷刺(讓執政當局聯想到政權的歸), 也因為全劇以「閩南語」發音(牴觸執政當局打壓「方言」的政策),但不確定是否也因為劇中含有同性戀娼妓──按照官方的長期習慣,一看到同性戀和娼妓,要不是馬上打壓,就是故意視而不見。
《望你早歸》長期沒有被關心同志的讀者討論,原因之一是遭禁,之二是同性戀是劇中配角而非主角,之三是劇本在文學史中一直是被邊緣化、被忽視的文類。重新珍視《望你早歸》也就有了修補文學史(不限於同志文學史)的多種意義。妙的是,一旦把《望你早歸》放在1970年代呈現男同性戀的多種台灣文本之間,就可以看出來它是異數。我曾經在〈誰有美國時間〉這篇文章指出,1970年代描繪同性戀的台灣文學作品幾乎都曝露出對於美國(含實際的美國本土,以及繞著美國打轉的各種幻想)的執迷(執迷含愛,恨,以及愛恨交織等等)。然而王禎和(台大外文系出身,對西洋文學嫻熟,在《美人圖》、《玫瑰玫瑰我愛你》強力抨擊美國)偏偏沒有在《望你早歸》留下任何跟美國有關的線索。其他同時期作品掛念「中美關係」(這裡的「中」,是台灣)、跨國移民;《望你早歸》在乎「城鄉差距」、島內移民:劇中腳色(除了警察)都是只能說「閩南語」(王禎和用詞)的社會邊緣人,只能在台北橋下的圓環等工作,很難在「國語」稱霸的台北存活。
「撿破爛」維生的阿立哥收養少年「啞巴」阿貴為子(用後見之明來看,這齣戲也凸顯身心障礙和多元成家的課題),但阿貴走失。阿立只好報警,卻跟警察發生三種衝突:阿立只懂閩南語,但是(明明能懂閩南語的)警察堅持要用國語;警察認定阿貴是啞巴,但是阿立堅持阿貴很正常(拒絕啞巴這個稱號帶來的汙名);阿立跟阿貴沒有血緣關係,但警察不懂阿立怎麼可能疼愛不是自己親生的孩子。(這三點對於2015年的台灣人來說也好眼熟。)
「望你早歸」這個劇名是指阿立哥希望阿貴早日回家。問題是,窮人何以為家?家是什麼?阿立哥認為,家這個場所就是要讓孩子接受良好教育,迴避學壞的亂源;如果孩子跟鄰居學壞,就不惜搬家。早在阿貴走失之前, 阿立哥就以一再搬家為苦──他發現跟他同樣是社會底層的鄰居汙染了阿貴。這對鄰居是先前提及的流鶯吉雄,以及兜售春宮照片的黑狗。阿立曾經在阿貴身上發現「這種脫褲濫, 這種妖精打架,這種拉撒照片」「不怕你將來長不大!」勤於教育孩子並且搬家的阿立,就像是孟母,或者該說是李漁的「男孟母」。周慧玲編導的《少年金釵男孟母》 就脫胎於李漁的名著,也可說是《望你早歸》的表兄弟。
雖然說阿立尋子是這齣戲的主線,但副線才搶戲。阿立將貧窮解讀為溫馨倫理劇和悲劇,但壞鄰居吉雄和黑狗卻解讀為喜劇和鬧劇;前者兩種劇的基調是追求成家(這個家似乎必須跟性隔絕)的溫情,後者兩種劇的態度則是成家不得遂改而追求色情(同樣,彷彿色情跟家相剋)的自暴自棄。但是這兩名男子的自暴自棄妖豔表現可能是台灣文學中「敢曝╱發妖」(camp)的前鋒之一。黑狗在街頭賣春宮的台詞是:「精彩精彩╳伊娘絕頂精彩……你來我往好一場妖精打架」;

《梅蘭梅蘭我愛你》封面
吉雄每一次「嗲聲嗲氣地唱」(如劇本要求)〈梅蘭梅蘭我愛你〉,就形同對當時台北社會進行猛烈諷刺攻擊。就經濟的階級而言,吉雄等人活在1970年代初期的貧窮線下,但是〈梅蘭梅蘭我愛你〉卻在歌頌飯飽之餘的情慾;就語言的階級而言,吉雄等人是被打壓的閩南語使用者,處於國語的霸權陰影下,卻偏偏唱這首國語歌曲來拉(男同性戀的)客。或許這齣劇就是在暗示:〈梅蘭梅蘭我愛你〉這樣的國語愛情歌曲就是一方面忽視社會的貧窮常態,一方面公然賣淫。
紀大偉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比較文學博士。作品曾獲聯合報文學獎中篇小說首獎與極短篇首獎等。著有短篇小說集《感官世界》、中短篇小說集《膜》,以及評論集《晚安巴比倫》,編有文集《酷兒啟示錄》《酷兒狂歡節》,並譯有小說《蜘蛛女之吻》《分成兩半的子爵》《樹上的男爵》《不存在的騎士》《蛛巢小徑》《在荒島上遇見狄更斯》等多種。現為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專任助理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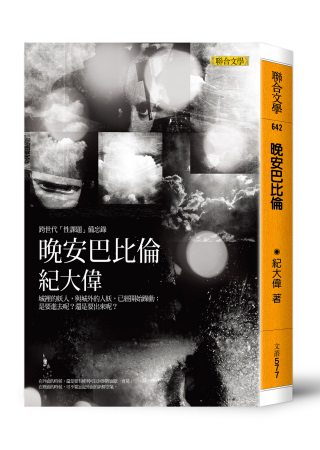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