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次見到契老師是素描課的休息時間。我走到他面前,佯裝自然一鼓作氣地說出口:「老師,聽說你在找模特兒,我想來應徵。」
他把雙手背在身後,斑白的鬍鬚爭先恐後地攀爬出粗獷的面部輪廓,他的眼睛瞇得細細的,快速用無形的 X 光從頭到腳把我看透一遍,表情沒有任何改變。那沉默的幾秒鐘我好像聽得見他腦子裡有齒輪緩緩轉開,喉嚨連動著一生的老痰咕噥我沒法立即辨認的聲音。
「下週四來。」然後他這樣說。

剛開始工作的時候還不大瞭解自己的身體,有幾次選錯了姿勢、放錯重心,時間未到手腳便開始不濟事地顫抖,他會從口袋裡掏出銅板來幫我定位,偶爾碎念我的體力太差。他在談話舉動的時候就像我初識他那樣,表情很少,但我老覺得他這樣隨性的人,五官不該僵硬。
一直要到跟了他第二年,我才感覺他的臉部肌肉逐漸放鬆。這堂課的主要組成是動畫科系的學生,有時也有教建築的老師靜靜走進、靜靜作畫。我們在教學大樓最邊緣的空教室上課,緊掩大門的午後他通常話不多,放任我播放任何瘋狂的音樂,也放任學生以各種素材與工具自由發揮。有陣子一位洛杉磯來的客座教授史蒂夫會跟課,他人來瘋起來就用很破的英文神祕兮兮地說起他的哲學,說繪畫精妙之處不在任何高深技巧,而在「氣」。
「什麼是『 Chi–––』?」史蒂夫禮貌地問。
他馬步一蹲打了圈假太極,然後咧開嘴傻笑,說,這就是「Chi–––」。
我後來在心裡偷偷叫他「契老師」。只兼了這門課的契老師鬆開之後會對我自嘲「妳的時薪比我還高」。春天會帶我們走出教室到後山畫畫。在學校的日子輕盈如幻,學生都對我體貼備至捧在手心,即使身在開放戶外一絲不掛,也完全不令人感到彆扭,只當自己是個公主,穿著公主的新衣,被一群溫柔的武士愛慕保護。這使我出了社會之後讓別人畫畫有時難免感覺落難,那落差可達公主比妓女那樣傷心地極端。

契老師是西班牙回來的,試著問起,他只賊眼一彎說起女人與紅酒,從來也沒說過什麼藝術大論。後來有人告訴我,契老師有一座鐵雕收藏在北美館,我知道那雕塑,看過不會忘,它的線條狂野而又優雅,在俗民熙攘與洪荒密語之間擁有一種大氣的平衡感。回頭我於是好奇再問起他關於作品的事,他只淡淡地說:「生病很久,就休息一陣,沒在做大型雕塑了。」
我沒敢問他生什麼病,他倒是吸了口菸,從皮夾裡抽出一張重大傷病卡,病名那欄只填了四個字:「妄想狀態」。
「那時候跟中邪一樣,我父母帶我求神問卜,說我被日本一位瀕死的藝術家高人附身。」他自若地說,「後來還真的飛到日本去找他。」
他沒繼續告訴我日本之行的細節,只在灰中帶燼的眼神之中獨自再次飛越那座海洋沉默起降。「好一點之後學校請我來教課。但一開始的時候開車來上課都得叫我太太跟著,坐在副駕看著我,不然好幾次都想直接衝下山崖。」
這不是我第一次遇到醒著夢遊的人,像身上早已留下記號那樣,只要遇了第一個,此後接二連三,更多他們輕易從人群中嗅到我,帶著各自的奇想次元來敲門而我忘私迎入。他們之中有的遭我無情背棄,有的掏出利刃廢了我的聲音,有的如常生活,有的已歸返塵土。契老師是當中與我能夠保持最美妙距離的一位,我們最親密的時刻是他冬天來家裡吃火鍋的夜晚,他坐在地板的長墊上喝了幾杯酒,面前的煙灰缸都滿了,粗礪的手掌來回撫摸賴在他懷裡不願走的白貓。
離開台灣之後我寄過一次明信片給他,並不確定他是否順利收到。我記得自己特意寫了些熱辣辣的話說很想他之類的,我想要他得意炫耀。我喜歡這樣對待他,或許是因為謎底揭曉那天我忽然對他感覺親近了,恍然大悟那些失去的表情其實是被藥吃盡,隨波逐流的豁達是大劫餘生後的了然放棄。「妄想狀態」這四個字聽來時序永久且漫長,使我想起某次讀自己的藥單,發現服用的過敏藥副作用是「感覺幸福」。我很難抵擋這種慘烈的浪漫。
我時常以為自己至少可以陪著夢一段,我支著頭傾聽十足荒謬並偶爾閃現漏洞的故事,任他們枕在我的手臂,偶爾順順他們無人理解的逆毛。誰能篤定我們眼見的一切都是真實呢,或許眼前這人所說的、絕對不可思議的言論,才是充滿洞見的真相,是萬物之間隱而不顯的祕密。這種錯差的感知好幾次使我跌跤,有一次真正釘住了我的心臟。復生之後我終於確認自己並不屬於一生心愛的妖物,只是個微小平凡的人。
「我們活了好長。」
昨天夜裡站在北平東路的騎樓和許久未見的導演重複這句話,好幾次。我們捏著手上的啤酒罐,只看著對方說話。台北的天氣並沒有回憶裡那樣糟糕,幾個漂亮的黑衣男女走進小方盒藝廊,又彎著腰走出。我們以一種午後新聞式的口吻報告相交的朋友星圖,相撞與逸離的、結局與預兆。
「一起裸體的同伴好難找。」她描述完最近的一個新作品之後嘆了口氣,「可遇不可求。」
「可遇不可求。」我重複她的結論,我們彼此點點頭。我不怕裸體,但我看待肉體並不如她那樣無差,生性虛華,沒有辦法成為她的同伴。
與導演相約之前我剛剛才和一名夢遊人道別,他踏破碎石荒原才華不遇,無盡美夢與壞夢刻蝕他的臉頰,使他削瘦幾乎成鬼。我與他進行了很長、但縫隙很大的對話,他正在一點一點好起來。至少我想要他一點一點好起來。這次與他道別,我的肩上並不留有急切與傷感,我的嘴並未說出甜美的承諾,轉身走入捷運現世,竟毫無隔閡芥蒂。意識至此我見了面便開口問導演,讓我喝點啤酒吧。
導演的笑容與過去幾無二致,她從里昂走來,手臂紋上電影的倒影,徒手在黑樹枝上刻下對永恆的愛的祝福,遞給了我。然後永愛破滅的我們在東德重遇,揹著行囊一起走進寒風中的小餐館,牆上的電視播著十年前的突梯 MV,我們捧著喝了高腳杯裝著的 Macchiato,走回街頭,繼續遠離彼此的軌道,又低低看著,愛著,我們無限大而滿是歧途的宇宙,那些以虛弱吸入心之痛楚的黑洞,恐怖之美無與倫比。勿忘得逝,我們這些最終游刃於現實的人哪,輕巧拂去的神聖與汙點總有如夢來人為我們忘情穿戴,Memento Mori ,藉此得活。

羅浥薇薇
八○年代出生。台灣苗栗人、左營長大。
現職為幼兒電視轉播與保育員、不自由創作者,未來不詳。 著有小說《騎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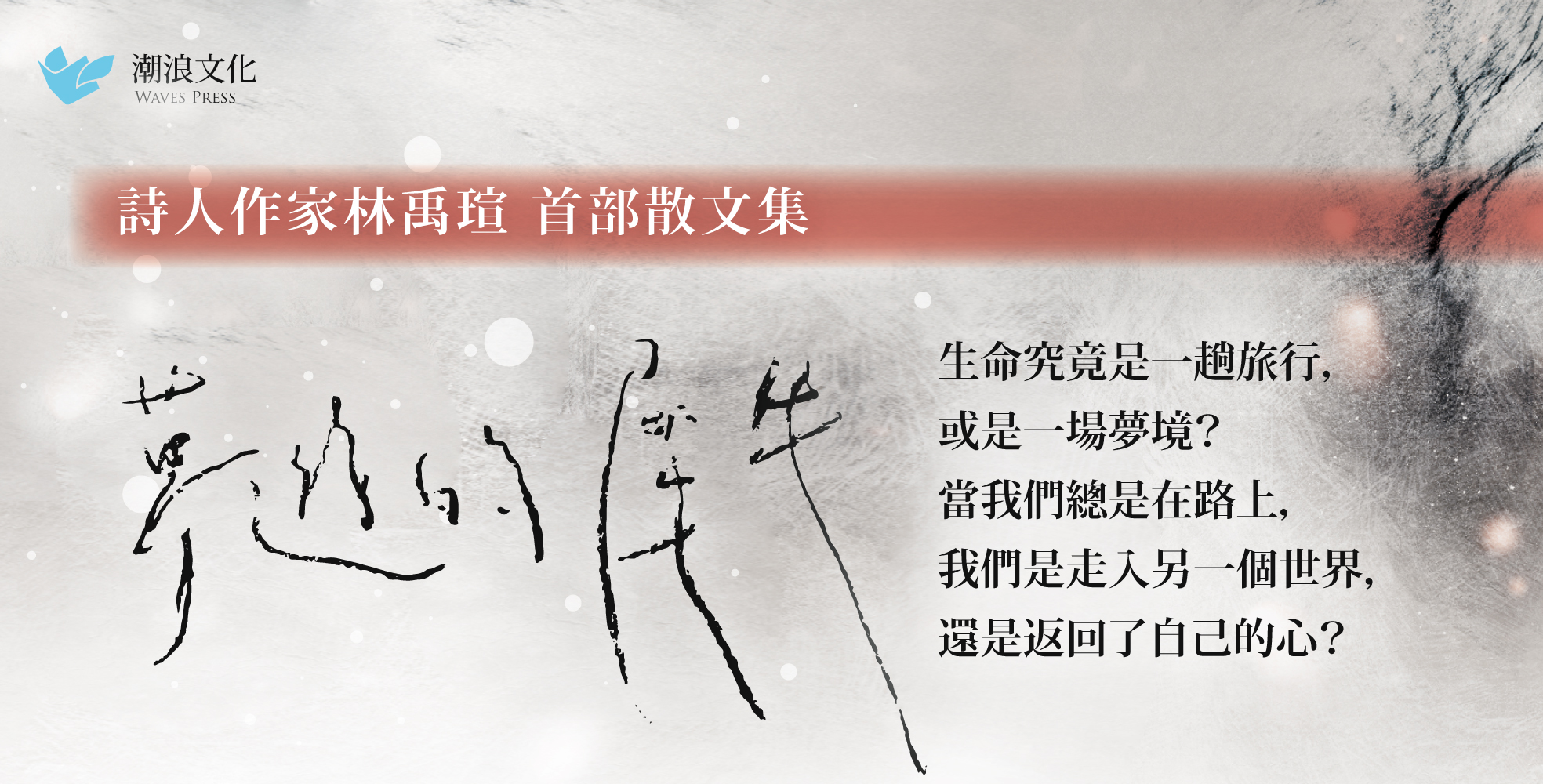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