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事翻譯五十年,景翔作品遍及小說和電影,他也寫詩、寫影評,擔任過《中國時報》副刊編輯、《民族晚報》編輯、《時報週刊》總編輯。即使是不特別注意譯者的讀者,也一定看過景翔的翻譯。他的能量豐沛,擁有大量的譯作產出,許多經典電影字幕,例如《越戰獵鹿人》《性.謊言.錄影帶》《當哈利碰上莎莉》,都是出自他的譯筆。如何讓人物對話流暢,轉化那些對白裡的意在言外,讓觀眾能夠跟隨鏡頭的腳步,愛看電影的景翔都能準確掌握。片商更曾經打出「字幕由名影評人景翔翻譯」作為宣傳,可見他的深厚功力。
如同他對自身工作紀律的要求,他將翻譯過的書籍按照出版順序排列。五十年的翻譯生涯,產量如何?他笑說,「如果包含用其他筆名發表的『私生子女』,大約有八十多本。」
回想多年來的工作過程,他想不起來有拒絕過任何出版社,「有人來找我就翻,比較不合適的作品就當是『磨筆』。」
出版業界都習慣於景翔的手寫稿,但近年來他受帕金森症氏病之苦,字越寫越小,開始改為電腦打字。在翻譯美國新銳作家凱文.鮑爾斯的《黃鳥》的時候,連打字都有點辛苦,他嘗試口述錄音,再找助理幫忙打字。
「口述的東西會比較鬆散,打好的稿子還要重新校正,仔細修改,修飾起來才會有更好的東西。」突然想起了什麼,他問坐在旁邊的出版社總編輯瑞琳說,「沒有耽誤到你們的時間吧?」鮑爾斯的文字被評論有海明威之風,即使語言淺顯,卻隱含深意,如何兩者兼顧地寫出來很不容易。瑞琳補充,書中有一句在描述天空的雲,英文原文是說「天空像墓室一樣」,景翔運用自己的感覺,譯成「天空的雲像裹屍布一樣」,讓譯文像是有機體,讀起來具有生命。
「想辦法進到作者的世界裡,跟他比較接近。」景翔說,每次工作的開始,除了閱讀外,就是想辦法去貼近作者。最順的是約翰.哈特的《順流而下》,印象中一下子就進去了,人物、對話都很自然。最辛苦的則是《此情可問天》,「過程就覺得很辛苦,所有翻過的書裡就那本翻得最差,太挫折了。翻完這本曾經發誓說不翻英國小說了。E.M.福斯特本身就是一個怪人,英文也用得刁鑽。」
不過氣頭過了就好,他後來還是有翻英國小說,例如《英倫情人》。那麼,遇到卡住的時候會怎麼做呢?景翔笑出聲,帶著男孩般的頑皮回答,「丟書。」不過這狀況只發生過一次,就是那本《此情可問天》。
「做翻譯中文要比英文好。」他平常的閱讀還是以中文居多,也建議年輕的譯者要多看中文,「尤其是古典文學,看得很多的話,對於人物、用字都會有幫助。」避免放進現代流行用語,考慮到文字的傳承跟連結,對每字每句都推敲講究,他希望中文還是要有維持長遠的東西。此外,他喜歡推理小說,不僅翻譯過許多,也催生《推理》雜誌。「早期影響我最深的一本書,就是松本清張的《點與線》。我都用這句話形容:四分鐘的空白,給我一生的震撼。」最喜歡的推理作家是誰呢?在漫長的抉擇過程之後,他說:「宮部美幸。」
景翔年輕時寫詩,與瘂弦、洛夫皆為好友,去年出版唯一一本詩集《長夜之旅》,如同回憶錄,紀錄精彩澎湃的生活與情感,書中提及性傾向,被視為一把年紀才出櫃。他以輪椅代步,現身去年十月的台北同志大遊行舞台,一頭白髮加上樂觀笑容,他對台下的年輕朋友們說:「我從來不在櫃子裡啊!」現場報以熱烈掌聲。最近他也為基本書坊翻譯《男孩們的童話故事集》,將人們熟悉的西洋童話改編成酷兒睡前版本,涵蓋成長與自我認同,帶來全新的童話體驗。
而在保守封閉的台灣早期,景翔就以翻譯者的身分,自國外引進同志文學與有關性別議題的作品,帶來更多視角及出口。例如說景翔唯一取片名的電影《愛是生死相許》,便是美國主流電影中,第一部討論同志、同志社群及愛滋病的電影。
訪問的當時,微波爐響起「叮」的一聲,景翔面前多了一個馬克杯,裡面是七八分滿的中藥湯,附上吸管更加方便飲用。他本來在寫「寵物五章」,寫家中的狗、鳥、鼠、貓,因為現在滿口牙齒都拔了,只能吃流質的食物,但他依舊笑著,說,「再過一陣子可以寫『泥漿歲月』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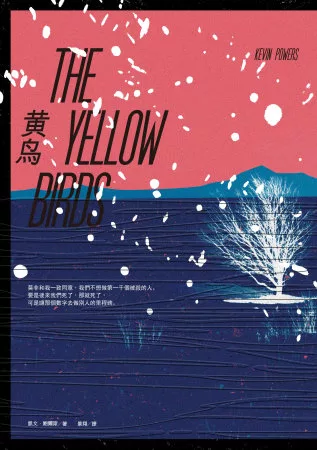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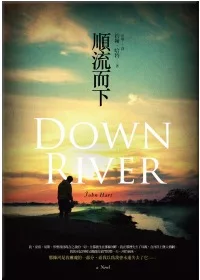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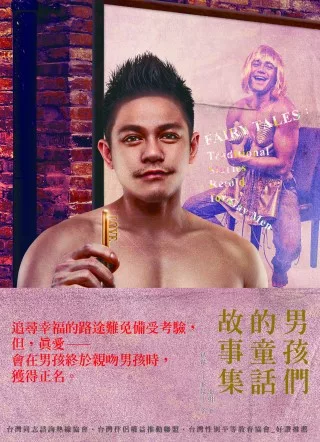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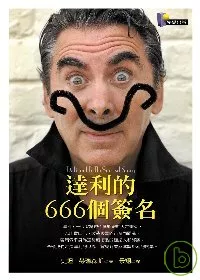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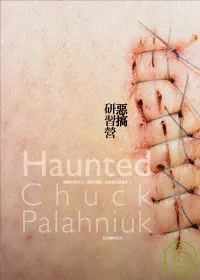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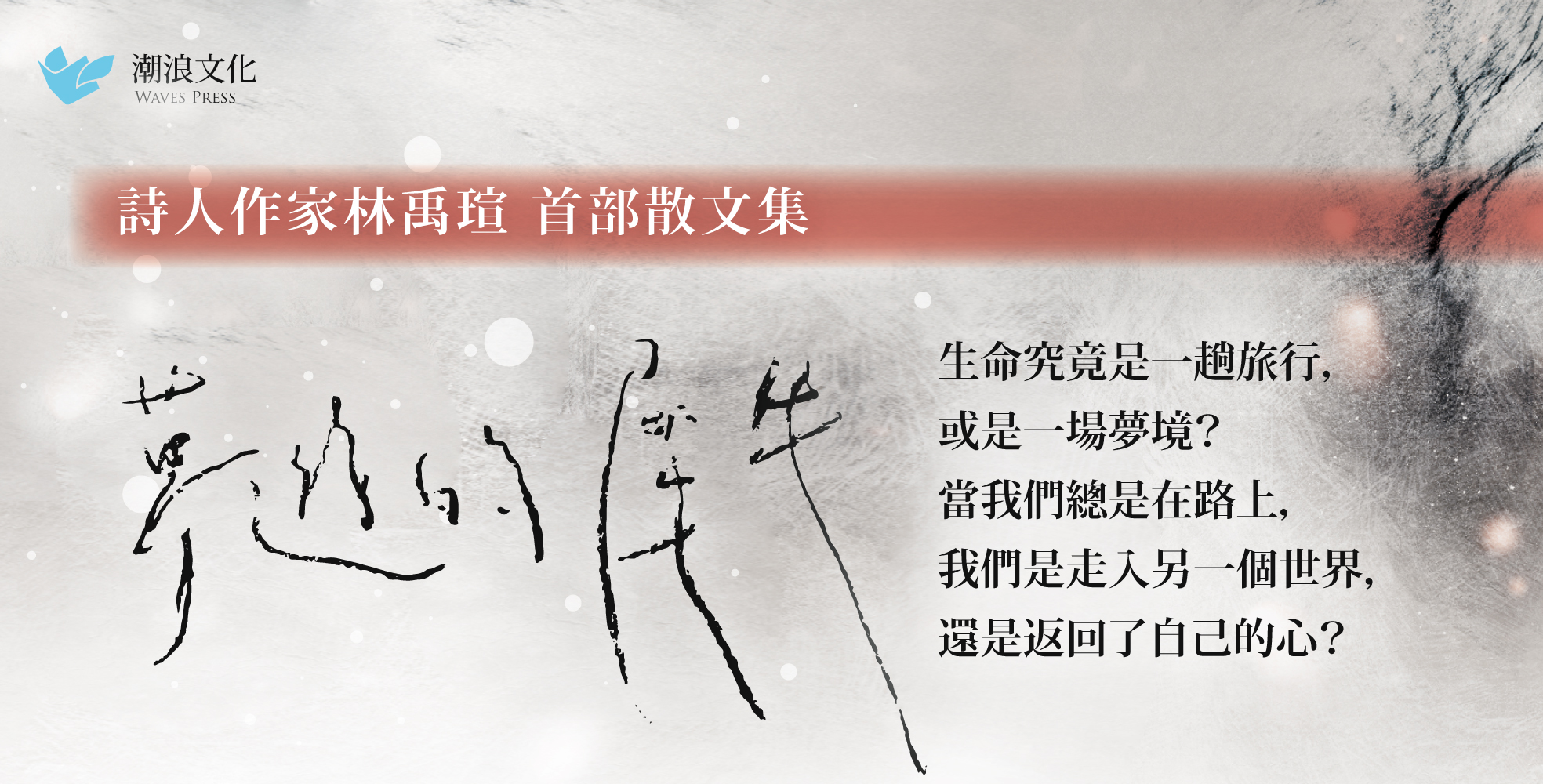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