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第一次見到他,是在「開卷十大好書」的頒獎典禮上,但就只是遠遠看他而已,那可是陳芳明,怎麼樣跟我這種小輩也不會有關係。第二次見到他,則是在台北故事館,他要主持我和吳明益的朗讀會。我和他早到了,主辦人把我們兩個安排在附設的咖啡館裡,面對面坐著。
「你要吃什麼?」陳芳明老師說。
「呃……那個,德國豬腳好了。」
「那我要吃雞腿。」
講完那句話之後,在餐點端上來之前,我個人立刻陷入一片死寂,那時我還沒到《聯合文學》任職,因此完全不認識本人,兩個人一點公私交集都沒有,就算從腸子裡挖挖看,也挖不出來任何共同話題。他問了問我是什麼學校畢業的,現在在做什麼,然後誇獎了一下我的新書寫得很好,連他太太都很愛看,他也在報紙上寫了推薦。他大概看我的表情相當不自在,甚至還親切地問了我結婚的事情。「怎麼辦!」我一邊必恭必敬地說謝謝,一邊心裡想,「對面坐的可是那個陳芳明,看起來就是非常嚴肅的樣子,我要是隨便亂說話的話,一定會被當作蠢蛋的,以後也別想在這圈子裡混下去了。」就這樣,直到那個活動結束之前,我一直處於高度「尊敬」的警戒狀態,等到我坐上捷運才從那狀態裡恢復過來。

從此之後,我一見到他,就會自然而然保持戒慎恐懼的模樣。這當然是因為我非常尊敬他的關係,而且如果直視他的眼神,會發現裡頭總是透露著一種強悍、不由分說的壓制力,但是一方面,不知道是從何時或是何處開始,整個情況卻變得有點歪掉了,像是以下這樣:
某次我們談完合約一類的正經事之後,芳明老師說:「我要開始寫小說了。」
「我聽說了,老師。」我說,「但真的,你不要寫,別來搶我的飯碗。」
「反正我要寫的是左營的故事,又不會寫到旗津和哈瑪星。」
「整個高雄我都要寫。」
「哪有這樣的,不行,左營我要寫。」
「好吧,那我要寫旗津、哈瑪星和鹽埕埔,左營就讓給你了。」
「好的,謝謝你。哈哈哈哈哈哈哈……」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我雖然以擅說渾話在友儕間見長,但卻敢沒大沒小到這個地步,而他居然也相當配合地笑個不停。
上個月,我跟芳明老師去北京參加兩岸青年文學會議。因為他實在太受歡迎了,總是一大堆中國學者圍著他,我沒什麼機會跟他說話。某天晚上吃完東來順,聽說有幾個作家要去他的旅館房間續攤喝酒,我也跟著混去。一進房間,向陽老師就在一旁起閧要我講個笑話來給大家聽。我很快想起一個超簡單的沒大腦網路笑話:
小明的媽媽叫小明起床,小明賴在床上說:「我不想去學校。」
媽媽說:「為什麼?」
「因為同學不喜歡我,老師也討厭我,所以我不想去!」
「怎麼可以這樣,今天是開學典禮耶!」媽媽說,「而且你是校長,怎麼可以不去!」
我講完的一瞬間,不騙你,芳明老師立刻爆笑出來!(而且他有多愛這個笑話呢?第二天一早,他還捉著會議的工作人員,把這笑話又講了一遍。)正當我得意洋洋,覺得自己把氣氛炒得很熱的時候,鍾文音老師忽然對著他說:「小明?那是在說你嗎?同學不喜歡你,老師也討厭你。」
「完了!」我的腦中一片慘白,眼睛無法視物,「文音老師您小姐的反應也太快了吧!而且為什麼網路上不寫小華,偏偏要寫小明啊!」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芳明老師大笑說,「我是所長,又不是校長,所以不用去參加開學典禮啦。」
回到台灣,在桃園機場等著提領行李時,我和他站在一起,繼續開著沒什麼腦子的玩笑。他一邊打簡訊一邊說行李這麼慢,一定是因為我們不是坐商務艙的關係,所以行李故意要慢一點給我們。然後我就搭腔說,對啊,坐商務艙的人領了行李之後,還會特別回頭看看我們的行李是不是出來了,要是太快出來,他們會覺得很沒面子。
「哈哈哈哈哈哈哈……」芳明老師又笑個不停。
我看著他,心想也許正因為他是個笑點這麼低,對任何事物都懷抱寬闊理解與諒解的人,才能夠先熬過身在異鄉無法回國的黑名單歲月,等到回來之後仍然衝勁十足地一一達成學術與創作的驚人成就。這個月,他窮盡心力寫就的《台灣新文學史》總算出版了,(老天啊,總算。)在可以預見的未來裡,我們幾乎不可能再見到另一本同樣等級與規模的台灣文學史著作。但我私自認為,或許未來總是會有人寫出另一本台灣文學史,然而芳明老師對台灣文學發展所抱持的樂觀心態,強調此刻的台灣文學正是集合了華人文學所有精華,無論語言、技巧、題材,充滿著最強能量的歷史觀,這才是最令人著迷的魄力之處。當然,必然會有人不同意這樣的歷史觀,正因為這樣,這才是只有陳芳明才能教給我們的東西。
一個笑點低的人能夠完成的巨大事情,真是難以想像啊……我要學起來!
〔陳芳明作品〕
王聰威
小說家、《聯合文學》總編輯。著有《戀人曾經飛過》《濱線女兒──哈瑪星思戀起》《複島》《稍縱即逝的印象》《中山北路行七擺》《台北不在場證明事件簿》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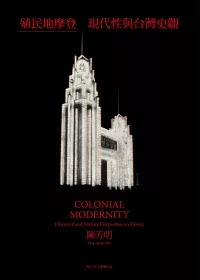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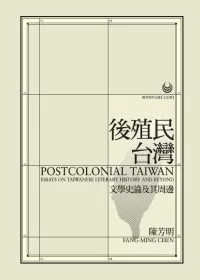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