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國華裔學者林松輝(Song Hwee Lim)的代表作是《電影同志:當代華語電影中的男同性戀再現》(Celluloid Comrades: Representations of Male Homosexuality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Cinemas)。這本書名應是跟美國著名同志電影專書先行者《賽璐珞衣櫃》(Celluloid Closet)致敬;《賽璐珞衣櫃》的紀錄片版本在台灣流通許久,我們叫它《電影中的同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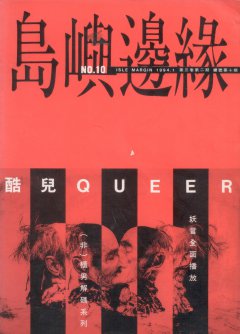
《島嶼邊緣10酷兒QUEER》書影
(提供/紀大偉)
(提供/紀大偉)
我承認《島邊酷兒專號》──正如許多古往今來的刊物一樣──讓初生之犢賺到沽名釣譽的機會,也同意「酷兒」這個新造的身分標籤──就如各種別的標籤一樣,如「北一女校友」、「台灣住民」、「憤青」等等──必然會突顯某些人並排擠另一批人。
年少荒唐事並無足掛齒,但我想強調「酷兒」這個詞的功用。台灣解嚴後社會洋溢了「命名」、「正名」、「去污名」的欣悅感;在這種氛圍中,在各界出現的「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如「同志取代了同性戀,酷兒在後想參一咖」)現象其實可以想像,也應讓人樂見。從以前到現在,我都相信「酷兒」一詞的功用,是提供在同性戀和同志之外,另一種想像與選擇的可能性。在同性戀一詞曾經壟斷相關人事物,而同志後來也形同壟斷的台灣情境中,酷兒提供了一些別的出口。我不敢說酷兒可以取代同志──我覺得同志跟酷兒的關係是分工大於競爭的。時至今日,這兩個詞已經顯然分工了:我們不會把「同志婚姻」說成「酷兒婚姻」;我們說某些人有「酷兒風格」而不說「同志風格」。這樣的分工未必讓人人滿意,但我覺得也還不錯。
林認為酷兒在台出現是一種「後結構主義」的表現,而他本人顯然對酷兒進行針對後結構主義的批判。他認為酷兒一詞推崇了「(文化)雜種」的概念、酷兒的推動者只要一看到文化雜種就自我感覺良好、並不體悟在文化雜種之後還有繼續投入政治改革的空間與責任。原則上我同意林對於後結構主義和雜種的批評──以當前台灣電視傳媒為例,今日的觀眾組成分子更雜了(很多外配和大陸人)、電視台口袋裡的音影資料更多元了,但我們看到的電視內容可能比1990年代的節目更扁平狹隘。
但在「原則上」之外,我也要補充「實質上」的面象:畢竟在酷兒生成當時,那個脈絡並非只有學院內的後結構主義,而還有學院外的解嚴。在那時候強調「文化雜種」、「搞怪」、「耍酷」是必要的,因為台灣當時還在緊抱「文化道統」、還在敬重蔣介石的銅像。與其說原則上台灣太愛文化雜種了,不如說我們到現在還不夠愛惜雜種的人事物。
林題目所指的翻譯、挪用應是指酷兒翻譯了英美的Queer、挪用了Queer和Gay的對比。這樣說是沒錯。但我也想指出,林在擔心酷兒亂搞Queer的時候,他所不擔心的同志其實也進行了翻譯、挪用。
大家都知道,同志一詞是香港人帶來台灣的,擺明挪用中共的同志,跟「同志仍需努力」的孫中山吃豆腐──但這種十幾年前的促狹意味,時至今日已經不再好笑、絕不顛覆。我們曾經以為把同性戀稱為同志是佔了中共的便宜,事實上佔便宜這種好康都是我們自己在肖想的,同性戀者的語言遊戲從來沒有在中國國體身上動過一根寒毛。當我們沾沾自喜以為北京也有很多同志時,北京也當然可以「整碗端去」地想:是啊,香港、台灣的確滿滿都是我們的同志,跟我們都一樣。
「酷兒」未必很酷,「同志」未必挪用成功,我竟然懷念「同性戀」這個舊詞了,那種「1970年代、1980年代初期」的老味道。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比較文學博士。作品曾獲聯合報文學獎中篇小說首獎與極短篇首獎等。著有短篇小說集《感官世界》、中短篇小說集《膜》,以及評論集《晚安巴比倫:網路世代的性慾、異議與政治閱讀》,編有文集《酷兒啟示錄:台灣QUEER論述讀本》、《酷兒狂歡節:台灣QUEER文學讀本》,並譯有小說《蜘蛛女之吻》、《分成兩半的子爵》、《樹上的男爵》、《不存在的騎士》、《蛛巢小徑》、《在荒島上遇見狄更斯》等多種。現為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專任助理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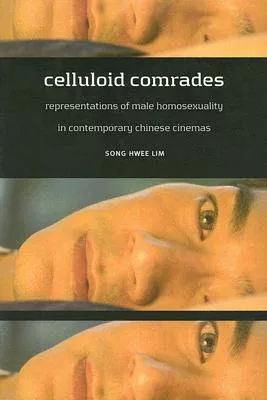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