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起佩津在書中寫,「應該要好好悲傷的時刻,我卻用旁觀者的眼光,試圖避開那些情緒。」壓抑、抽離、淡定,幾乎盈滿了分明是悲傷故事的《卸殼》全書。
我跟佩津相識於三一八學運時,我總覺得,每個會投入社運現場的人,必然有其原因,但大概因為當時共有的社會氛圍,我未曾仔細探究是什麼讓她從學生時代就走上街頭。認識五年,佩津偶爾會丟來她的創作,她的文字裡有濃重得化不開的情緒,雖然壓抑,但卻能看得出有亟欲脫離命運的部分、也有對母親心疼不捨卻也不知該如何相處的部分,就像我們這個時代的孩子,不滿意上一代塑造的親子關係,但又難以割捨。於是,如推理小說般,我興起了溯源的念頭,一方面希望佩津聊聊她的背景,讀者才能理解為何她的情感既濃重又壓抑又逃離,另一方面,我也想藉機處理親子關係。佩津說,媽媽會看她的臉書與她的文章,有時會反饋給她,她記錯了哪些家族故事;我想,若能趁此把父母的故事記錄下來,或許也是打開彼此關係的一種方式:了解媽媽過去發生了什麼,也讓媽媽趁機了解佩津。
佩津有著記者的本性,我們討論寫作主題到一半時,正是她接到媽媽腦出血、終止學業趕回高雄的時刻;她比編輯還要能對自己狠心,想帶著錄音筆去採訪母親,把自己的人生化為過往在壹週刊寫的那種人物報導。有些時候我會有濃烈的罪惡感,覺得身為編輯冷血無情,佩津反過頭來安慰我沒什麼。
之後的情況就如書中所寫,佩津的媽媽接受各種民俗療法,母女關係越演越烈,然後愕然止於跨年夜的燒炭自殺。佩津曾在臉書上跟我開著玩笑,說書寫著寫著,怎麼就變成癌症家屬書;我還說透過陪病書寫家族史與個人史,隱約帶到時代背景,感覺不錯啊。接著關鍵的一月一日到來,我讀到了佩津媽媽過世的消息,假裝輕描淡寫地問候她、跟她聊聊,她回答我當日下午在靈堂前擲筊跟媽媽聊天:「反正她說現在心情好了,這樣就好。」語氣一樣抽離壓抑。
其實讀完全書,不難了解佩津的壓抑從何而來:疏離的母女關係,背後是現金卡盛行時留下來的卡債風暴;更往前推一點,則是景氣繁榮的大時代下,一名母親為親人作保,卻遭背叛而債臺高築的故事。佩津的故事有著高雄產業興落的見證、有單親媽媽撫養小孩的艱辛、也補足了記者夏傳位《塑膠鴉片》之後每個卡奴的後續。在惡劣環境下長大的小孩,擁有如此豐沛的愛是表面,不安造成的遺世獨立,才是真實。
去年年底,我陪佩津去見正式帶她跨入記者這行的李桐豪。李桐豪形容這書彷彿核爆現場,但卻書寫得淡然。佩津說:「這是一種保護自己的策略吧,我很習慣把情感都壓抑住。」跟佩津認識太久太久了,讓我幾乎忘記這本書寫的是一個父母雙亡孤女的故事。
透過推薦文,許多人跟佩津表達過祝福了;但我不太知道該怎麼說,因為獨立堅強的她,好像強迫著自己,讓自己什麼都不需要。我常常會想,我還能幫作者做什麼、還能幫上什麼忙;或許趁此表達一點心意,只要有編輯能做的,請告訴我,我隨時都在,歡迎妳來。
陳怡慈
大塊文化主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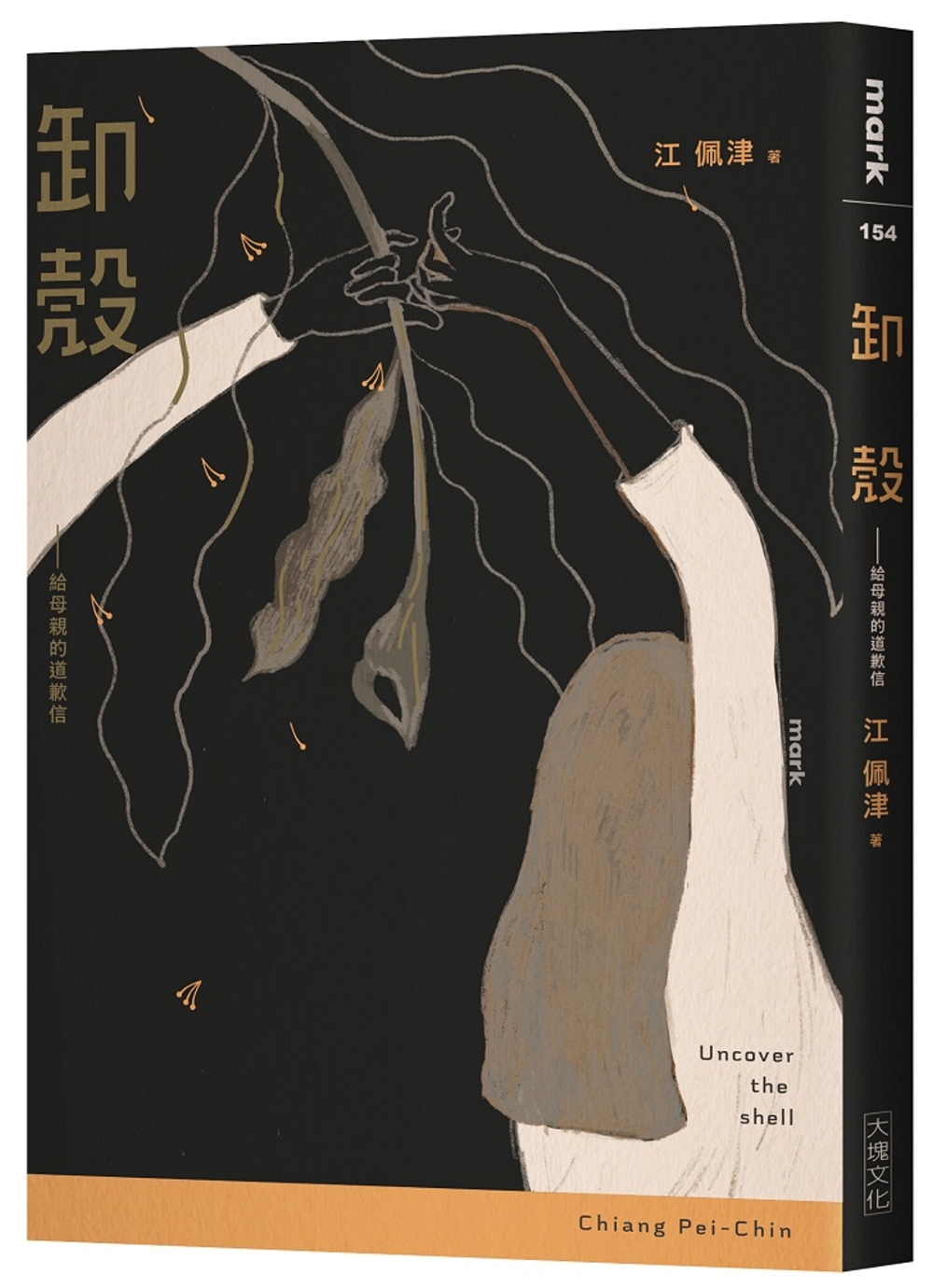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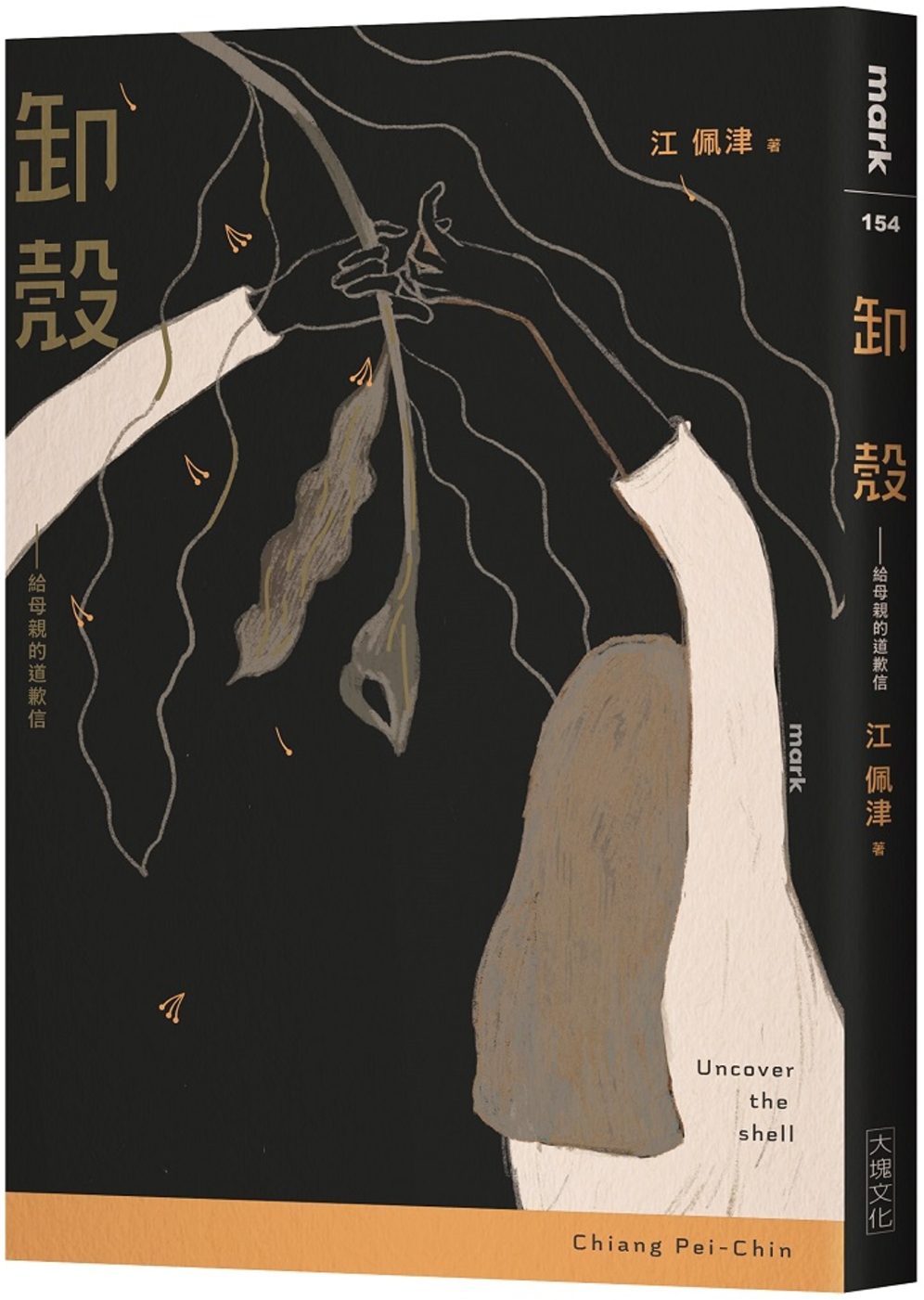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