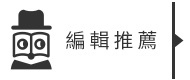前言
向晚的涼風拂過林木茂密的山丘,趕走了白天的燠熱,也帶來了跟我一樣渴望涼意的鳥兒。他們成群飛來,啁啾鳥鳴聽似歡笑,讓我也不得不報以同樣雀躍的笑聲。他們全圍繞在我身邊,有雪松太平鳥(Cedar Waxwing)、貓鳥(Catbird),還有色彩斑爛、像是閃過一抹彩虹的藍知更鳥(Bluebird)。此刻,我們嘴裡都塞滿了莓果,也同樣發出幸福的咯咯笑聲,讓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親切,全因為我也叫羅賓(Robin,亦為知更鳥名)的關係。灌木叢中結滿簇擁的莓果,各在不同的成熟階段,有的紅、有的藍,有的則是酒紅深紫——數量多到你隨手一摘就可以撈到一整把。還好,我帶了一個桶子,只是桶子愈來愈重。鳥兒只能將莓果裝進肚子裡,不知道他們載了這麼多的貨還飛不飛得動?
富饒的莓果好像純粹是這片土地賜予的禮物,而不是我掙來的:我既沒付費,也沒有付出勞力,從計算價值的數學來說,怎麼看都不是我應得的報酬。然而,他們卻送到我面前——連同陽光、空氣、鳥兒一起,還有聚集在積雨雲高塔上的雨水,遠方的風暴看似山雨欲來。你可以說他們是自然資源或生態體系提供的服務,但是知更鳥與我卻將其視為禮物。我們嘴裡塞滿了莓果,心裡也滿懷感恩之情。
我的喜悅有一部分來自出乎意外的驚喜,因為我從未想過會在這裡採到這些果子。土生土長的服事莓(Serviceberry , 拉丁學名為Amelanchier arborea)結出的果實又小又硬,口感偏向酸澀,只是偶爾才會出現一株結有甜美果實的樹叢。今天,在我桶子裡的大豐收是來自西部的品種——A. alnifolia,通常稱為薩斯卡通莓(Saskatoons)——是我的農民鄰居栽種的,今年第一次結果。他們生產莓果的熱情與我不相上下。
薩斯卡通莓、六月莓(Juneberry)、鰣魚灌木莓(Shadbush)、鰣魚花莓(Shadblow)、糖李子(Sugarplum)、薩維斯莓(Sarvis)、服事莓——這些都是唐棣屬(Amelanchier)灌木果實的眾多名稱之一。民族植物學家現在認為,植物的名稱越多,在文化上的重要性就越高。這種植物因其果實可食、可以入藥,又在春天的第一道曙光來臨時綻放花朵,點綴仍然覆蓋白雪的銀白森林邊緣,因此備受人們喜愛。服事莓又有日曆植物之稱,生物周期完全依照季節性的天氣模式。唐棣花開代表地面已經解凍,鰣魚正在逆流而上——至少是河水清澈無冰、足以讓鰣魚產卵的時候。
像服事莓這樣的日曆植物,對於必須與季節循環保持同步的傳統原住民來說,至關重要,因為他們每年都要穿越自己的家園,來到替他們準備好食物的地方。他們並沒有為了自己的方便而改變土地,反而是改變自己;隨季節而食是一種向豐饒致敬的方式,也就是在豐饒的時間和地點來迎接他們。在農產品倉庫和雜貨店的世界裡,你可以在需要的時候買到想要的東西。我們付出了相當大的經濟和生態成本,強迫食物來到我們身邊,而不是順應農產品自己的時間,取用大自然給予我們的東西。這些服事莓沒有受到脅迫,他們的碳足跡為零。也許這就是他們嘗起來如此美味的原因——他們一年只有在這個時間出現——這些短暫的夏日小酌,不留下任何傷害的餘味。
「服事莓」的名字雖然有「service」一詞,但是卻與「服務」或「服事」沒有任何關係,而是來自薔薇科的一個非常古老的名稱「Sorbus」(花楸屬),後來逐漸變成「sarvis」,最後才有了「service」。雖然名稱並非源自其服務,不過這種植物確實提供了無數的產品和服務——不僅是賜予人類,也賜予許多其他自然界的公民。他完全支持生物多樣性。鰣魚灌木是鹿和麋鹿的首選食物,而對剛出生的昆蟲來說,也是早期花粉的重要來源,更養活了一系列的蝴蝶幼蟲——例如:虎紋鳯蝶(Tiger Swallowtail)、總督蝶(Viceroy)、線蛺蝶(Admiral)和旑灰蝶(Hairstreaks)等——還有眾多在繁殖季節靠著食物熱量果腹的鳥類。
人類也依賴這些熱量來源,尤其是原住民的傳統飲食習慣。服事莓是製作乾肉餅的關鍵成分。將乾莓果與乾鹿肉或野牛肉一起搗碎成細粉,再與因此提煉出來的脂肪結合,最後固化成原始的能量棒。這種高度濃縮的保存食品可以在缺乏食物來源的季節中,提供充分的營養,並且易於運輸、儲存或攜帶。乾肉餅也成為傳統貿易經濟的一部分,多餘的食物熱量可以換取當地無法獲得的其他商品。
無論生長在何處,服事莓都是原住民飲食方式的一部分。我是波塔瓦托米民族(Potawatomi Nation)的成員,該民族是五大湖地區的一個阿尼希納貝族(Anishinaabe peoples)。我曾有幸在傳統饗宴上吃到用服事莓做的紫色糖漿蜜餞,激發了我的味蕾以及對這種祖傳食物的記憶。
在波塔瓦托米語中,服事莓叫做「Bozakmin」,這是最高級的形容詞,代表最好的莓果。我用舌頭淺嚐了一顆,立刻認同祖先替他取的名字,真是再貼切不過了。想像一下,如果有一種水果嚐起來像藍莓,但是又混合著蘋果那種令人心滿意足的分量,再加上淡淡的玫瑰水和帶有杏仁味的種子咬起來的那種細碎的嘎嘣脆。那風味不像在雜貨店裡可以買到的任何東西:狂野、複雜,帶有一種你身體認可的風味,是身體一直在等待的真正食物。當我在吃服事莓時,幾乎可以感覺到體內的粒線體正在快樂地手舞足蹈。
對我而言,「Bozakmin」這個字裡最重要的部份就是「min」,這個字根是「莓果」的意思,會出現在波塔瓦托米語的藍莓(Minaan)、草莓(Odemin)、覆盆子(Mskadiismin)等詞彙中,甚至連蘋果(Mishiimin)、玉蜀黍(Mandamin)和俗稱野米的菰米(Manomin)裡也有。這個字是一種啟示,因為它也是代表「禮物」的字根。在替那些大量賜予我們善意的植物命名時,我們體認到這些是來自植物親屬的饋贈,體現了他們的慷慨、關懷與創造力。阿尼希納貝語的語言學家詹姆斯‧武克里希(James Vukelich)教導我們說,這些植物的饋贈「體現了植物對人類無條件的愛」。他寫道,植物傾其所有,賜予那些有需要的人,「聖人和罪人都一樣」。
我情不自禁地凝視著他們,將這些閃閃發亮的寶石捧在手心,忍不住心中滿溢的感恩之情。面對這樣的禮物,感恩是直覺的第一個反應。這種感恩之情流向我們的植物長老,並投射到雨水、陽光,還有那些點綴著點點甜美果實的灌木叢——感謝有他們近乎不可能的存在,才讓這個世界不至於那麼苦澀。
在阿尼希納貝人的世界觀中,不僅將果實視為禮物,而是將大地提供的所有物資都視為禮物,從魚類到柴薪,不一而足。舉凡讓我們能夠生活下去的所有一切——編織籃子的木條、入藥的樹根、用來蓋房子的樹幹,還有我們書裡的每一頁紙張——都是由人類以外的生命所提供的;無論你是直接從森林裡採集收穫,或是藉由商業媒介,從雜貨店裡的架上取得物資,這一點都千真萬確,因為他們全都來自這個地球。當我們不再將這些物資視為物品、自然資源或商品,而是一種禮物時,我們跟自然世界的整個關係都會為之改觀。
在阿尼希納貝人的傳統經濟中,大地是所有物資與服務的來源,以一種交換禮物的形式分配給眾生:贈送一個生命藉以支持另一個生命。重點在於支持全體人類的好處,而不只是為了個人。接受大地賜予的禮物,就要擔負起連帶的責任,如:分享、尊重、互惠與感恩——時時刻刻都在提醒著你。
這種感恩之情遠遠不只是一句禮貌性的「謝謝」;不是一種自動的「禮節」儀式,而是察覺自己內心的虧欠感,足以讓你震驚到停下腳步來細細思量——讓你真正的體認到自己的生命是受到大地之母用她的身體來滋養長大的。當我的手指因為沾滿莓果汁液而變得黏答答時,讓我想到自己的生命必須仰賴他人的生命;沒有他們,我根本就不會存在。水是生命,食物是生命,土壤也是生命—-他們透過光合作用和呼吸作用搭配成奇蹟,成就了我們的生命。我們賴以生存的一切都流經這片大地,稱其為大地之母並不是一個空洞的比喻。我們放進嘴裡的食物是同時串連精神和肉體關係的絲線,因為我們的肉體獲得養分,精神則得到歸屬感的滋潤,這才是食物最重要的功能。我無權擁有這些莓果,但是他們就在我的桶子裡,這是一份禮物。
這一桶六月莓代表了數百次的禮物交換,才讓我的手指染成藍色:楓樹將落葉奉獻給土壤;無數的無脊椎動物和微生物交換養分和能量,形成腐殖土,讓服事莓的種子可以在其中紮根;雪松太平鳥留下了種子;陽光,雨水,早春的蒼蠅為花朵授粉。他們都是禮物交換的一部分,每個人都可以透過禮物交換來滿足他們所需。
許多原住民族,包括我的阿尼希納貝親戚和「長屋族」鄰居,都繼承了所謂的「感恩文化」;在這種文化中,人們生活方式的組成全都圍繞著對地球贈禮的認可與責任,無論是在儀式上或是實務上。我們最古老的教誨故事提醒我們,不表達感恩之情就會辱沒這份禮物,並帶來嚴重的後果。如果你狩獵了太多的水獺,等於是羞辱了他們,他們就會離開;如果你浪費玉米,就會挨餓。
細數你收到的禮物會讓人產生一種富足感,知道你已經擁有了所需要的一切。在一個總是敦促我們增加消費的經濟中,認識到「足夠」是一種激進的行為。數據顯示,地球上的食物熱量「足夠」供給八十億人獲得營養;然而,還是有人在挨餓。想像一下,如果我們每個人都只拿走足夠的東西,而不是遠遠超出我們的份額,結果會如何呢?透過分享我們所擁有的一切,可以滿足我們看似渴望的財富與安全感。生態心理學家已經指出,感恩的做法可以抑制過度消費。禮物思維所培養的關係減少了我們的稀有感和匱乏感。在這種充足的氛圍中,少了那種想要索取更多的飢渴;我們只取自己需要的東西,尊重贈予者的慷慨。氣候災難和生物多樣性喪失都是人類貪得無魘、無節制掠奪的結果。培養感恩之心可能是解決方案的一部分嗎?
如果我們收到禮物的第一個反應是感恩,那麼第二個反應就是互惠:回贈禮物。我可以送什麼給這些植物來回報他們的慷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