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到法國時,我住在聖敘爾比斯(Saint-Sulpice)的修道院宿舍,一面準備研究所申請資料,一面心想,該為日後的學者身分做準備,遂於書店添購專書,好作智性資糧。其中一本是法譯版的美國學者伊芙・可索夫斯基・賽菊克(Eve Kosofsky Sedgwick)九〇年代重量級作品《闇櫃知識論》(Épistémologie du placard)。那是我首次正式接觸普魯斯特,以一個被翻譯的語言,從一位酷兒學者的批判視角,進入《追憶似水年華》。
文章詳細內容不敷記憶。唯腦海裡存留賽菊克抨擊普魯斯特作為一名無法真正直視自身同志情愛(將主敘述者設定為異性戀),並選擇與主流文化掛鉤,以病態,獵奇,甚至負面角度描述書中作為同性戀代表的角色夏呂思的大致印象。
進入研究所生活,課餘時,終於在書店購買了《在斯萬家那邊》。
我坑坑疤疤地讀,普魯斯特的法文精深,語句結構繁複華麗,且長。許多段落得來回反覆推敲,才能大致捕捉作者的曖昧意涵。全書開篇一場景久久縈繞心頭,是敘述者回溯童年睡前,總苦苦希冀母親至床前獻上晚安吻。我被當中毫不扭捏,遮掩的,一種對母親的無限眷戀與依賴(近乎觸碰潛意識亂倫的慾望邊界或戀母情結)深感動容。
論讀書,尤其是讀《追憶似水年華》這種大部頭巨作,最重要的,許是找到個人與作者,與作品間的鑲嵌性。
我曾是只拜訪過斯萬家的第一冊讀者。真正讓我起心動念想認識普魯斯特的,是在法國電台podcast節目,聽聞一則關乎他與眾鄰居魚雁往返的介紹。普魯斯特長期臥病在床,飽受哮喘之苦,同時疊加高敏人特質,格外在意居住環境品質。
他曾寫信抱怨鄰居每隔兩日的做愛聲響(並將叫聲比擬作謀殺)。在著名的奧斯曼大道居所,他將臥房貼上軟木條降噪。他的樓上住了牙醫與其職為豎琴演奏家的妻子。普魯斯特寫了許多信,關於早晨的電鑽,關於他將於某幾日外出並希冀對方在特定時段維持寂靜的特殊要求。當他在知悉對方親屬於戰爭中喪命時,他也寫信聊表哀悼之情。他送花,好感激鄰居在特定日子配合他的任性要求。我開始好奇一位如此細膩至神經質的作者,他創作時的底蘊與原欲為何?他又如何去愛?
我重拾起《追憶似水年華》,不躁進地,一年保持閱讀一至兩本該作原文的速度。
《追憶》如同《一千零一夜》,是文學史上以敘事抵抗死亡的龐大計畫。在母親逝世後,普魯斯特才真正擎筆開鑿小說時光(正如多年以後的羅蘭巴特,在母親死亡後寫就的《明室》與《哀悼日記》,相片,成為普氏記憶錨點的重要素材)。小說家為疾所苦,心急如焚,只為保證能在生前完成龐大創作計畫。兩場銘刻小說家生命經驗的死,被折射進作品中,現實生活裡母親的死被鑲嵌在主角外婆過世的情節裡;阿佛雷德・阿戈斯蒂內利(Alfred Agostinelli)自駕飛機身亡一事則被轉品,琥珀般凝凍在小說中艾貝婷墜馬過世的安排裡(反觀作者自身的同志情慾,被濾鏡折射斜射在主敘述者與眾女性角色間;現實生活裡的男同志妒忌,更錯位式地,幻化為異性戀男子對女同志情誼的猜疑)。
小說令人折服之處,除了高超的文學技巧與敘事語言,尚有一點,即為去情節設定。無刻意安排,任憑時光作為書裡最重要的顯影劑。
推進敘事的主元素除了上述之死,更有位於對立面的,普魯斯特式的獨特之愛。
愛是嫉妒(jalousie),是苦難(souffrance)。小說家鄙友誼,重情愛,認為唯獨透過情愛,那因無法徹底占有對方,掌控對方而導致挫敗嫉妒引起的痛苦,直視此苦,將能引發個人的深層哲思(現實生活中,普魯斯特為了知曉心儀對象行蹤,甚至雇用過私家偵探;如此偏執的愛,徹底反映在《女囚》一書)。戀人間,他延續波特萊爾的感情觀,保留劊子手與受害者的相對位置,強勢弱勢的失衡關係。真正的愛拒絕被侵占,一旦客體被征服,情愛終將落入生活與日常的牢籠,被庸俗沖刷,成為厭倦(ennui)。普魯斯特式的情愛原型,許是最初斯萬家母親的晚安之吻,那關乎等待,挫折,哀傷與渴望(情愛本體論跟前,出櫃與否,賽菊克的批判,被多年後成為寫作者的我放置在作者與人物,真實與虛構的括弧間,成為文本裡,一種附屬而非絕然必要的探討條件)。
面對一部以時間為顯影劑,企圖以博物館式或人類學者之心囊括彼時社會符號縮影的龐大作品,我身為讀者所尋得的最適宜的觀看角度,即為同感,共感一種神經質,略為偏差,激烈的悲劇式的愛。以及同為操持文字,普魯斯特在面對死亡疾病時,選擇竭盡所能燃燒文學愛,那夜以繼日飛蛾撲火的決絕姿態。
作者簡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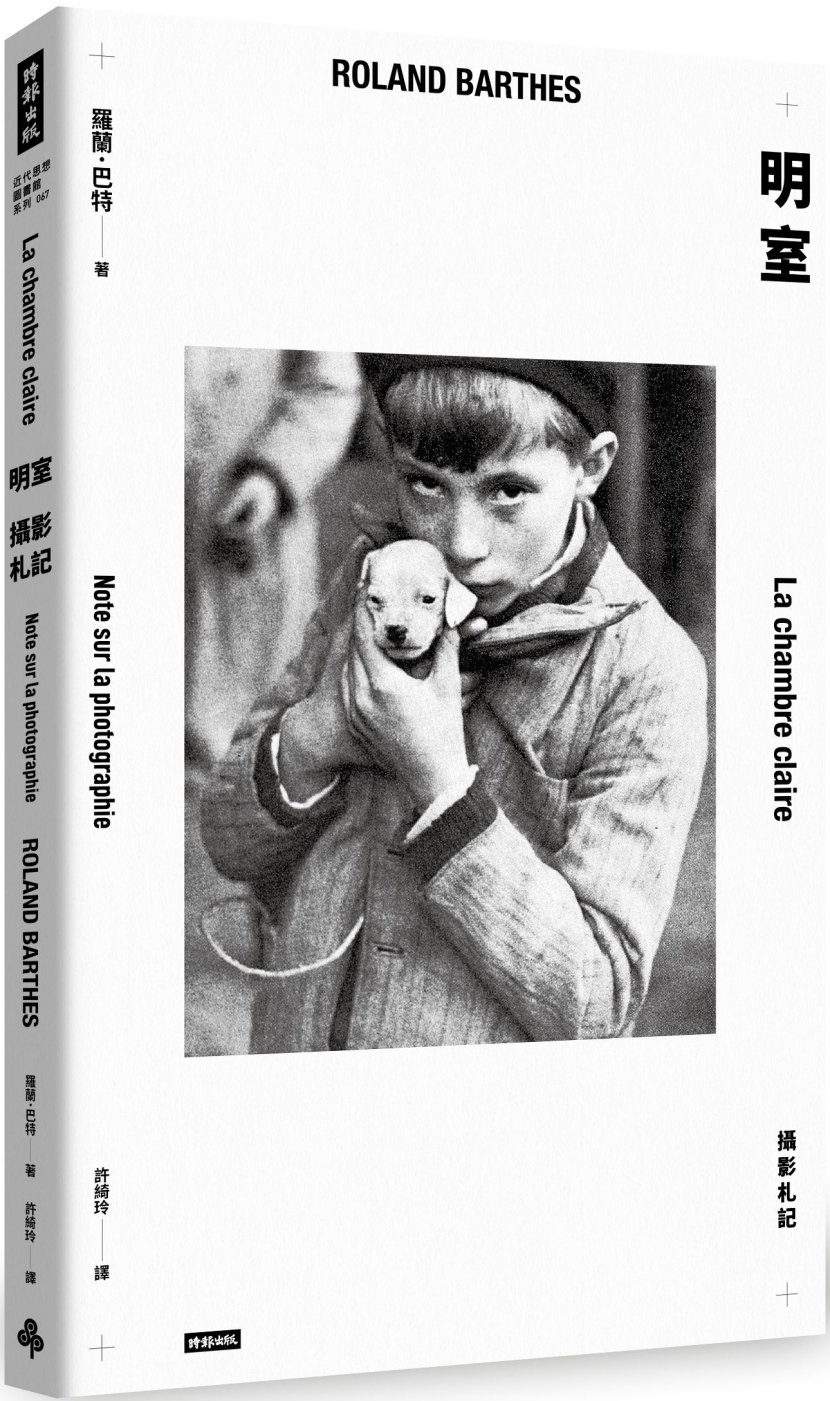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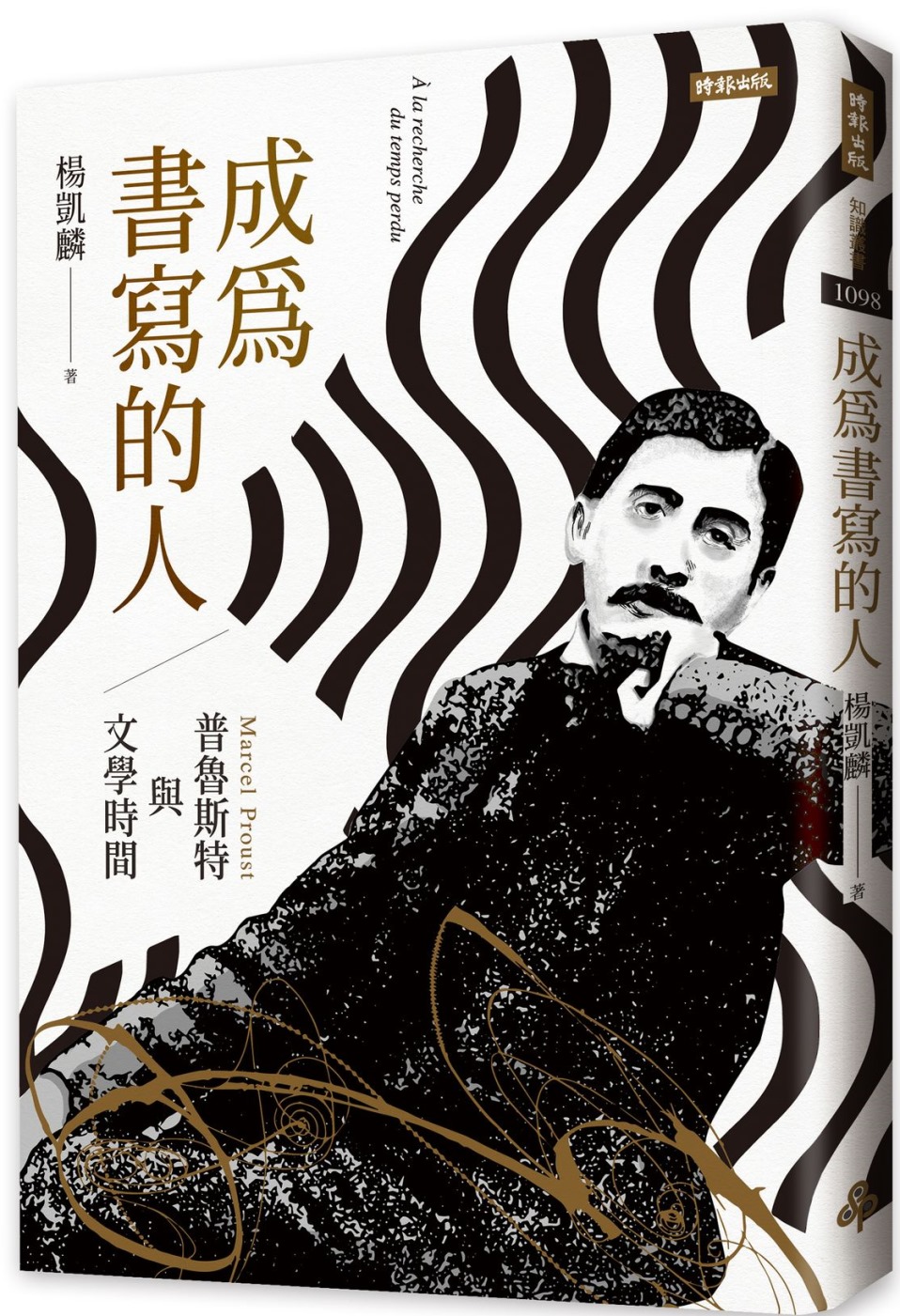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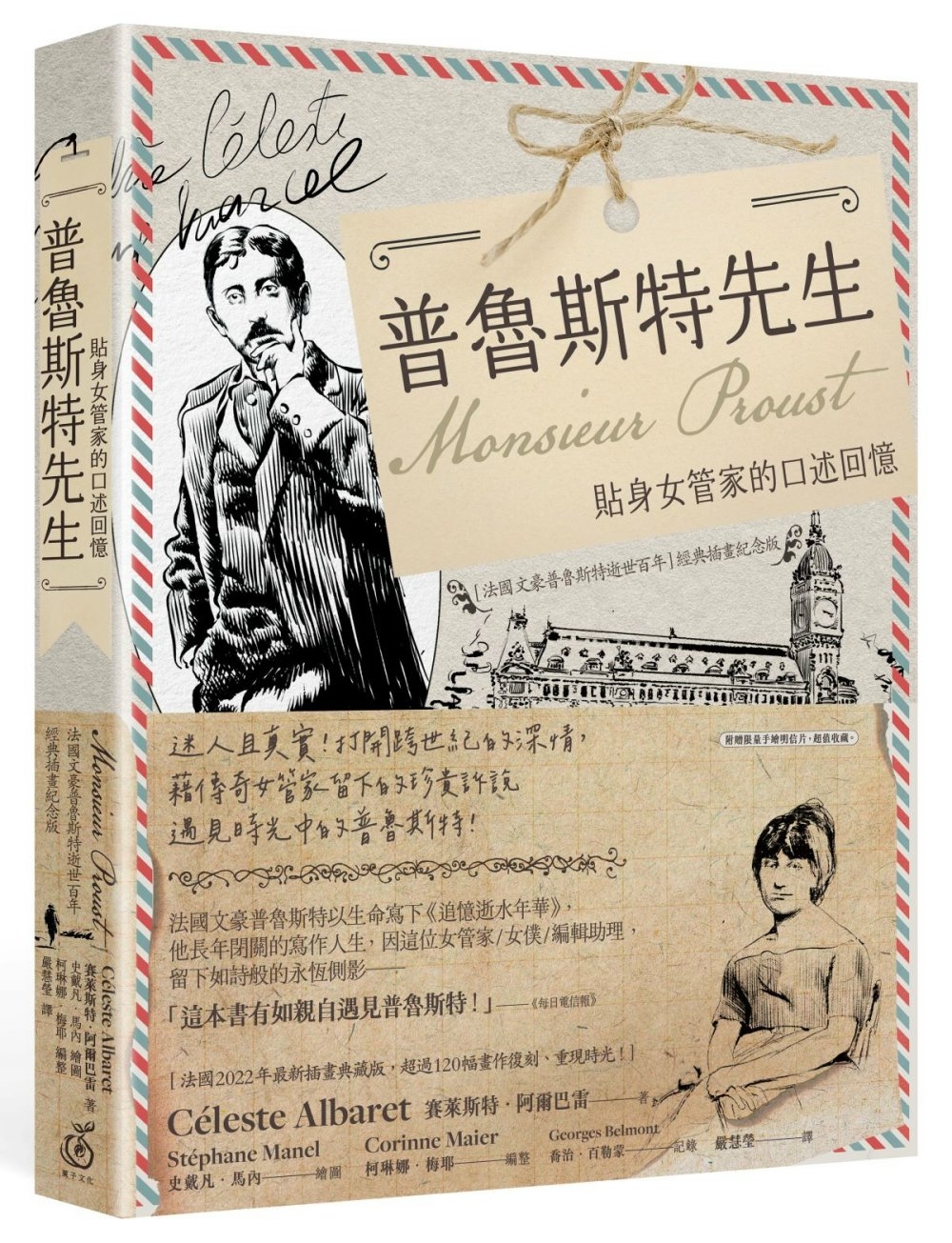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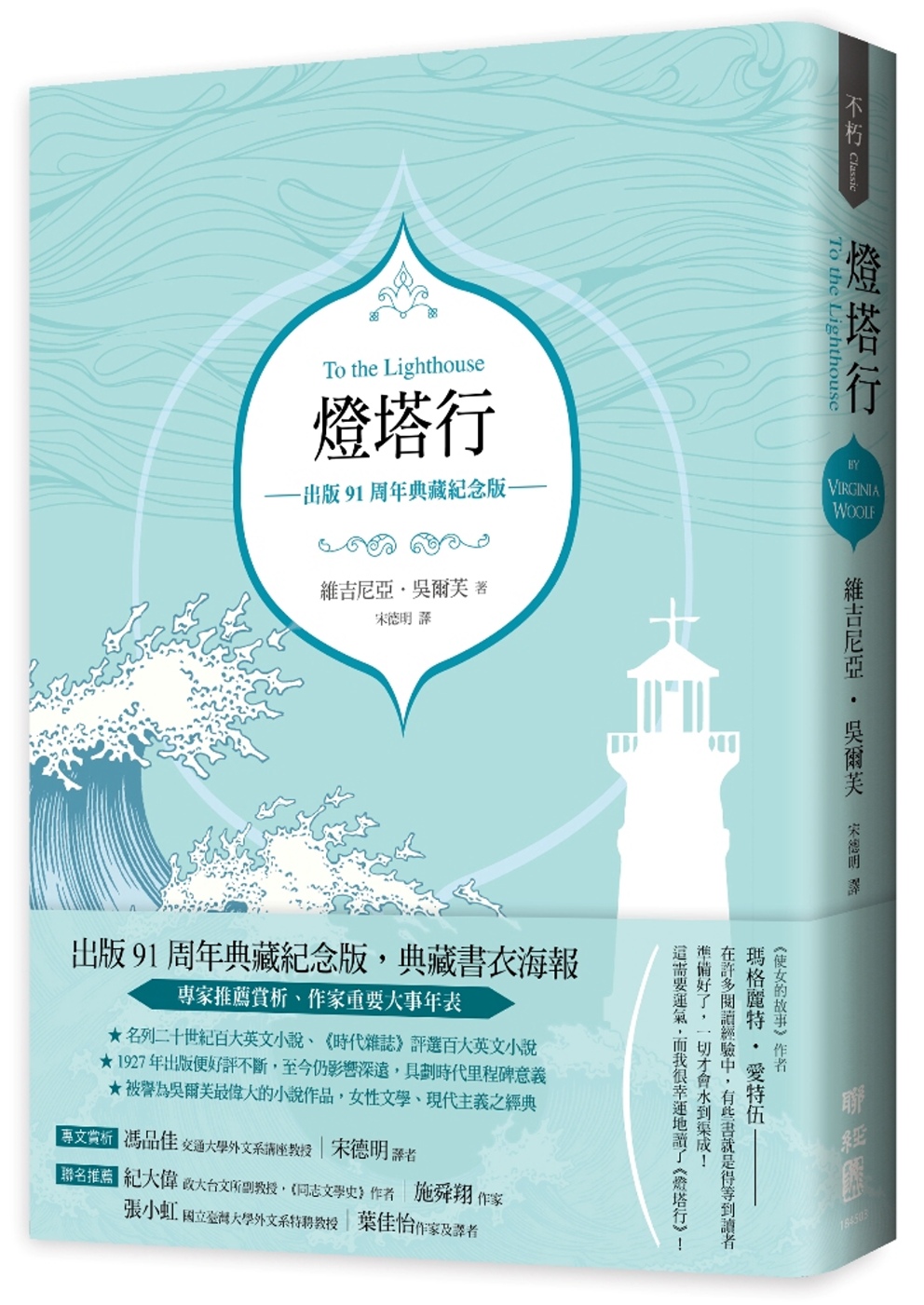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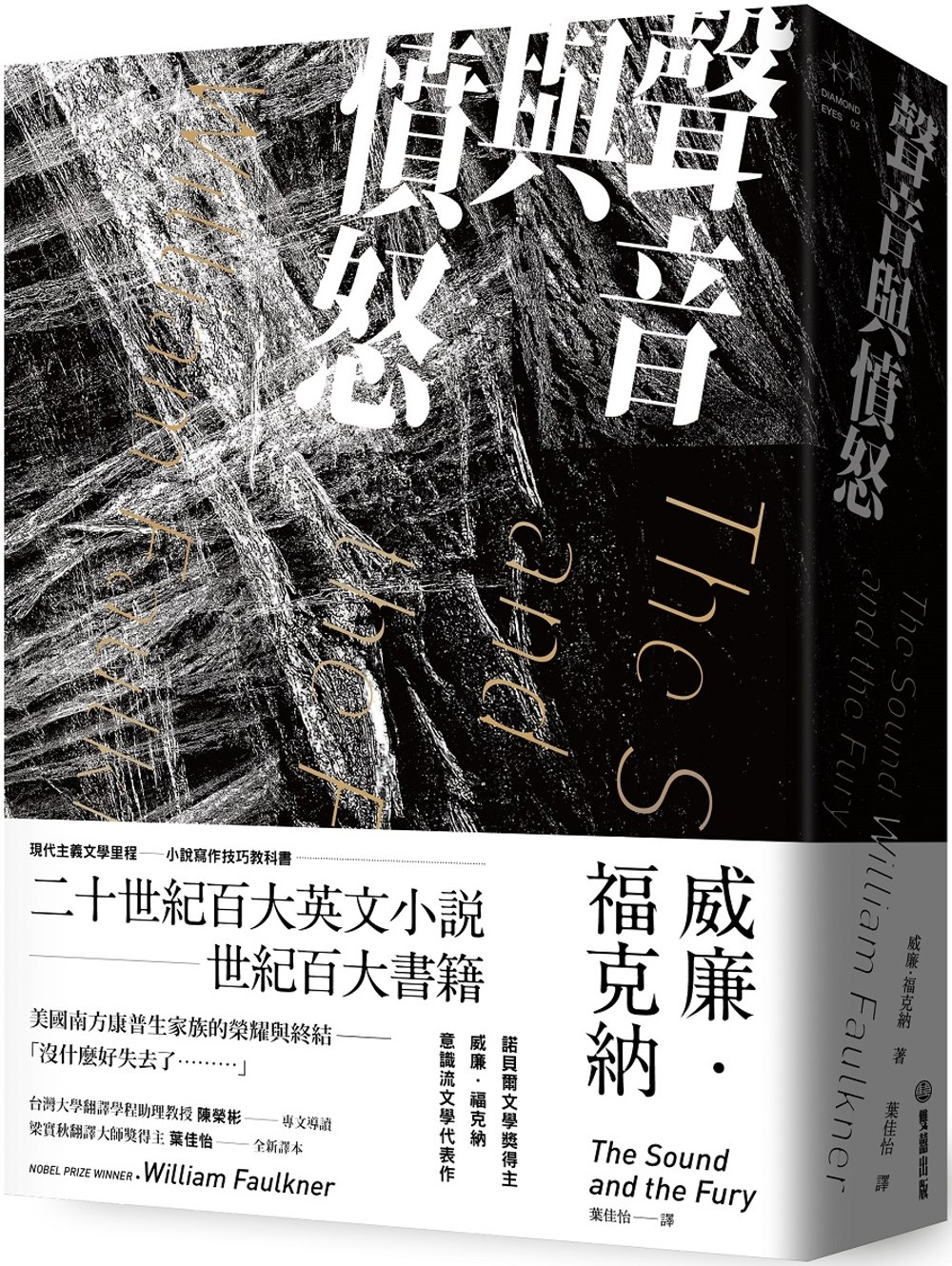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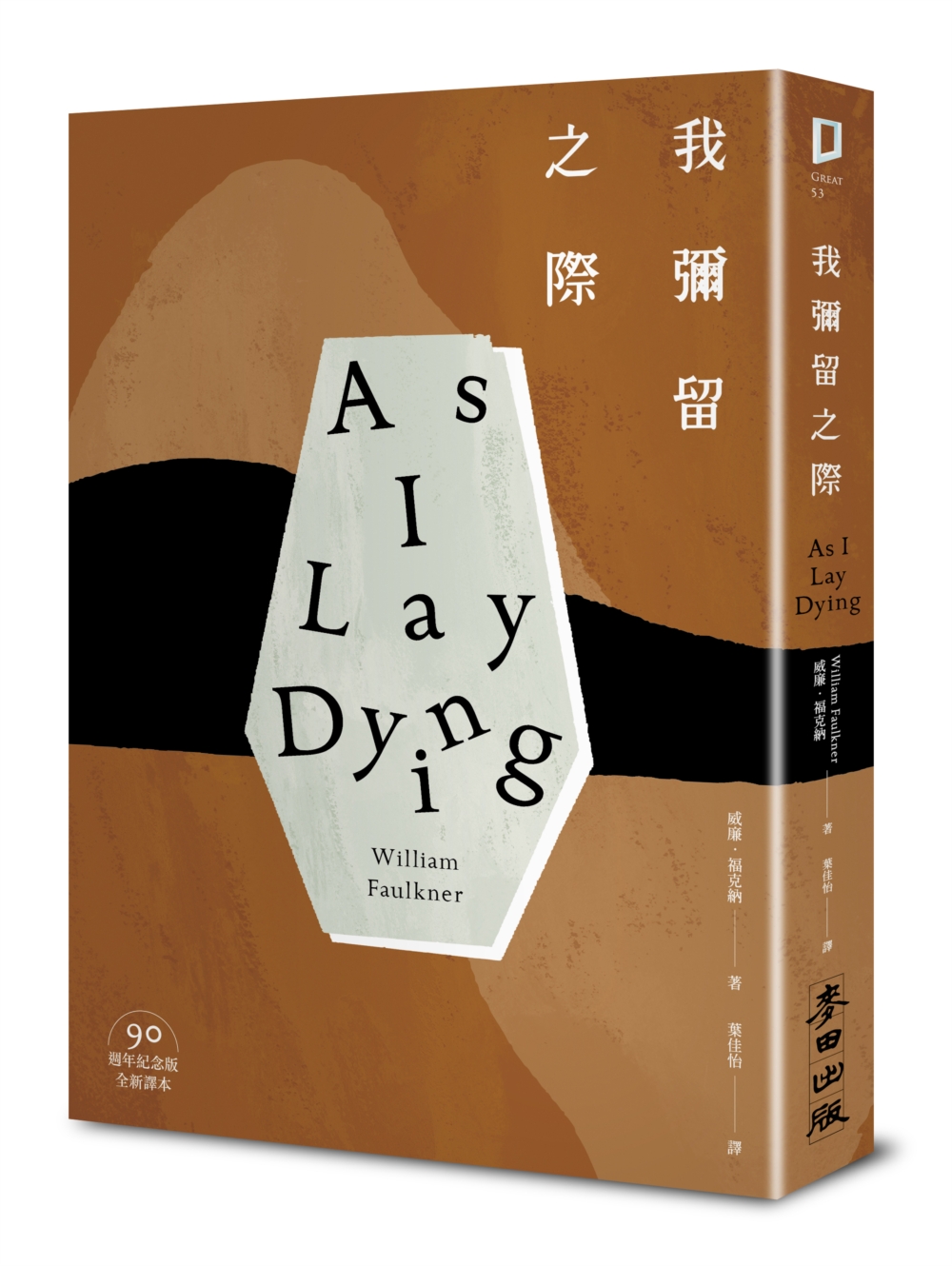
























回文章列表